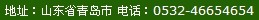|
山河埂 山下有河,叫山河;河边有埂,就叫山河埂。山河埂挡住了山洪对圩田、村庄的侵袭,埂上交通,坡面种植,老牛吃草,雀子欢叫,也是乡下一景。 小时候跟老保姆去她娘家陆家墩子,那兴奋相当于如今的自由行。过了老埠头,必经一座不知名字的大石桥,桥下山河,秋冬清澈见底,夏天暴雨后黄泥巴浆子直滚,一直滚到黄浒河,再跌入长江。山河埂和外河圩埂共同保护着天保圩和苏村圩。从乡下回家,老保姆经常领我从圩心里越过猫耳桥,再绕到山河埂上,顺便找点什么带回家,不空手,就是荻港人说的“跌倒了黄土都要抓一把”。印象最深的是捡蓖麻秸秆,土话叫蓖麻荄子。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码齐了,一大捆,瘦瘦的老保姆先蹲下身子,背到背上,再出劲站起来,两根绳子紧勒在肩胛骨上,脸上就有了细密密的汗珠子。 晚风吹来,山河轻漾,一老一小,沿着山河埂,上了大石桥,圆圆的太阳在江北平原慢慢往下坠,天边铺满了水红缎子。过了大石桥和老埠头,就能望见镇子。天黑前,老保姆把蓖麻荄子放进我家的小缸灶里,一阵噼里啪啦烟熏火燎,晚饭就香了。 姐姐说,你不要把山河埂说得太诱惑,小时候我也常去山河埂捡蓖麻荄子,要是闷热天,还会遇到盘成大饼样子的火链子蛇,直愣愣地看着我,好怕人啊。而从天保圩来的学生则告诉我:都是水泥厂,老埠头早就炸平了,山和田都没了,哪有山河?没了山河,还有山河埂啊?小姑娘语速飞快,剥毛栗子一样,我将信将疑,半天回过神来,只想起了张明敏的一句“河山只在我梦里”。 没去过的地方都是好风景。元旦前一天下午,学校放假,教工活动,我抓拍了几张同事冲刺的笑脸,就朝县城反方向的乡村骑去。我想绕峨山、浮山、峨桥三个乡镇一圈,晚上赶回来再参加组里的聚会。骑车独行也是我辞旧迎新的传统节目,属于一个人狂欢。过了平旷的沙园村,就看见望不到头的起伏青山,骑到近处,好家伙,原来这里也有一条和沙园路垂直的山河埂呢。 我把自行车推到高高的山河埂上,只见山河沿着山脚蜿蜒而行,河水清幽,流速缓慢,对岸山头竹林成片,霜叶染红,杂木森然。柳条临水处,有红衣女子在石铺子上洗菜,几只白鸭子在她旁边戏水。上游不远的河中央,有个小洲,静静地立着几棵树,水中倒影,纹丝不动,太阳斜照,丝丝光带,历历可数,仿佛老保姆给我做鞋子的绣花线。一切都如儿时山河埂情境的回放,我远观近看,左拍右照,痴痴傻傻,几乎泪下。 立秋后的第三天下午,天阴阴的,不太热,我又想骑车出去,去哪里呢?于是就想到曾经偶遇的峨山、浮山山河埂。 轻车熟路,和风微雨。这一回的山河埂之行,就像当年回陆家墩子一样轻松。沿着山河埂,穿过峨山,一直骑到现在属于芜湖三山区的浮山老山里,还发现了山河旁边远离城镇、古风犹存的小山村。一路上,我遇岔道就问路,逢村民就聊天,走走停停,声色田园,尽享惬意,几个细节,尤其难忘。 路过一个村子,山河埂突然一个下坡,我急忙刹车,可是破自行车的刹车声太过凄厉,就见一条受惊的黑狗,从门前猛地朝我扑来,狂吠不已,正在恐惧狼狈之时,主人老乡急忙追着黑狗一路大叫“作死啊作死啊!”及时阻止了袭击,又对我说“不怕不怕,吓了没有啊?得罪得罪。”惊恐过后,老乡的满脸皱纹和憨厚容颜,让我想起老保姆陆家墩子的大兄弟,那时我喊他“大娘舅”。“大娘舅”和“大舅母”养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勤劳忠厚,待我如家人。 一老乡给我指路,他说:“顺山河埂往前滚,过了大桥,淌淌就到了。”这一“滚”一“淌”,我听了非常受用,这不仅是最合情境、最本色的表述,更是对我的奖赏和鼓励呀。 山河埂上,还遇见一位大妈,她手里拿着两根刚摘来的长长的丝条,笑盈盈地对走在前面的老伴说:“老头子,我烧菜,给你晚上喝酒啊!”而“老头子”也转过脸来微微一笑,活脱脱就是青春版的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来到了河边……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今生今世,我的生命里,也许注定有一条永远的山河埂,你是山做的、水做的、土做的,你是老保姆、蓖麻荄子、火链子蛇,你还是受惊的看门狗,下酒的两根青绿的丝条…… 山河埂,你知否? 静秋 静秋,不是静静的秋天。 上完第四节课,照例说了“祝同学们春节快乐!”后,便开始寒假了。人一松下来,就容易放纵。晚上一直听歌,呼斯楞的《鸿雁》,降央卓玛的《西海情歌》,吉克隽逸的《带我到山顶》,还有王向荣的《走西口》《光棍哭妻》……真是“宁可傻一点,我也要音乐”。犯傻的结果是找不到入眠的方法,于是想到除夕下午要去墓地给母亲烧纸,天气预报说除夕可能要下大雪,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在狱中“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思路沿着雪的情境延展开去,翻过古竹岭分水岭牛歇岭,慢慢抵达江南古镇荻港老街的南门桥财神湾,最后,定格于“静秋”。静秋,是个美女。 她的美和我母亲相似,而她们的美又都和张爱玲早年的那张经典照片相似。论年岁她应该比我母亲小点,这些从小就识文断字的女性,穿衣讲究,铺床讲究,点点滴滴都讲究。在我遥远而模糊的记忆中,她特别喜欢抱人家的孩子玩,又是亲,又是疼,瘦瘦脸,白生生的,很光洁,细细眉毛,说话不是荻港口音,总是把到中街公家肉案子上“称点肉”说成“打点漏”,声音也细细的,和气,好听,发型记不清了,那年月没有烫发和披肩,好像就是“耳刀毛子”(齐耳短发),也好看,最神奇的是听说她还会开汽车呢。静秋就住我家对门,我们两家只隔了老街的几块石板条子。静秋,是个织女。 静秋和婆婆住一起,临街老屋两层楼,后面还连着一间披厦子灶屋。她好像没单位,婆婆也没,静秋就靠给人家用篾针打毛衣两人过日子。记忆中的静秋总是坐在黑魆魆的堂前方桌子旁边,一边打毛衣,一边看街上的行人,或者说一边打毛衣,一边盼着新的顾客上门。如果没有记错,她也曾经为我打过毛衣的,因为我母亲上班没时间,而静秋的工钱要的那么少,手又那么巧。只要看了人家穿的毛衣,不管花样多复杂,针子多繁琐,她都可以随手编织,一模一样,而且用时极短。如果冷空气要来,急着穿,头天送毛线,她一夜不睡,第二天就能让你穿上新毛衣。有一回晚上,她捧着毛衣到我家楼上二妈妈家串门,一不小心居然踩塌了老朽的楼板,轰的一声,连人带楼板还有马桶盖子一起掉了下来,正好掉到我母亲和姐姐住的房间地板上,斜躺在地上的静秋,脸色煞白,毛线团子直滚直滚,手里还紧捏着篾针和毛衣。 静秋的手艺,不知温暖了镇子上多少邻里街坊,她一针一针连缀起来的毛线,应该足以顺着德胜河通到长江,再随一江春水,连起京杭大运河,一直绵延到她遥远的故乡。静秋,是个坏人。她从一个美女变成美女蛇,来得平地春雷,猝不及防。据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大弄子民办小学读一年级的我,那一天在伙伴们的簇拥下,兴高采烈地爬到讲台上,架上板凳,踮起足尖,奋力扯下黑板上方叛徒内奸工贼的标准像,抠掉眼睛,然后戳在竹丝扫把上沿着荷花塘疯跑,呼朋引伴,义愤填膺,像过年玩龙灯一样幸福淋漓。想想可能那一天,大概就是静秋华丽转身的节点吧。据说她的夫君过去是个医生,是个军医,是个反动派的军医,所以她能够不是坏人,不是白骨精、美女蛇吗?尽管已经分开了,那也不行,谁要世上那么多好人你不嫁,非要嫁给反动派呢?只怪你自己前世未修,“人叫不走,鬼叫飞跑”啊。 静秋,是个歌者。 静秋本来是静静地织着毛衣的,自从我扯下标准像后,镇子上就“不是请客吃饭”了。因为我实在太小,也记不得静秋华丽转身后的种种情节和细节,反正比照那时候连我家房客夏老爹都因背不出“语录”而遭到厉声训斥的场景(夏老爹是个拎篮子到采石场卖油条的老人,一字不识,双目近乎失明,三代老贫农),就可以想象的到静秋的日子了。 听说是夜里天花板上的一条蛇把她吓坏了,于是她就不停地唱歌。白天唱,晚上唱,天晴唱,天阴唱,在屋子里唱,在大门口唱,打毛衣时唱,不打毛衣时也唱,别人要她唱她唱,别人不要她唱她也唱。她最喜欢唱的就是《白毛女》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风雪漫天,喜儿在深山,怀念众乡亲……”还有《歌唱二郎山》——“二呀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那是一首大气磅礴而又柔情似水的红色赞歌,赞美的是50年代初筑路部队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意志,旋律荡气回肠,极富艺术感染力。 夏日傍晚,老街的青石板热气未散,家家户户都从荷花塘或者德胜河拎来一桶桶水,泼在门前降温,也泼洗澡水,然后把凉床子搬到街边纳凉睡觉,大大小小的凉床子一个连一个,把财神湾中街德远街连成一条和德胜河平行的蜿蜒小河。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传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躺在润凉的竹床上边,静静地听静秋天天把歌唱,“二呀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雪花那个飘,年来到”,歌声绵长而高远,激越而低回,一直把我们唱到甜美的梦乡……静秋,是个逝者。 静秋病了,婆婆卖了房子,楼上楼下,鹤立鸡群,那么大的一座临街老屋,先当后卖,好像只卖了块钱。婆婆回到九华山附近的老家,静秋先是在后面的灶屋里过渡,等到约定完全交房的时候,她就无处栖身了。房子的新主人是建筑队瓦匠,夫妻二人忠厚朴实,他们当年送的盆景假山至今还是我家的风景,静秋没了窝真的不是买家的错。病了的静秋住在透风的灶屋里,雪花钻进来,温柔地铺在地上,灶上,床上。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到最后她居然把最脏的东西放进那口黄锈斑斑的大铁锅里煮了,那是任何人也无法理解和想象的。静秋的最后归宿,是黄家山下公路旁边那个废弃的砖窑洞。黄家山是小镇著名的乱坟岗子,那时谁要诅咒一个人,最毒的就是“你这黄家山埋的哎!”砖窑像个荒寒天坑,只有破败的弧形门洞有一点存身之地,可以铺些稻草,而沿着公路不远处,翻过牛歇岭,就是著名的建新劳教队采石场。她是白天走的,还是夜里走的,走的时候,她是想起家婆奶奶了,还是想起妈妈了,谁也不知道,只记得也是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也是欢天喜地年味渐浓…… 人类打造一个张爱玲,用了千年万年,而抹去一个准张爱玲,好像只用了童年的我胡乱扯下标准像时的那一瞬间。 降央卓玛背上的那两包水泥 不是冤家不聚头,晚上急吼吼回家,赶紧看男篮亚锦赛中韩直播。正在中场休息,原来上半场中国队已落后10多分,第三节一上来,依然梦游,眼瞅着大势已去,我脸发烫,心直蹦,赶紧调台,来点儿轻松的,不然要出人命了。 央视的另一个频道正在播降央卓玛专题,舞台中央,聚光灯下,身着藏装的她面对粉丝,回忆小时候经历。切入节目时,她正说到:我15岁那年,当了清洁工,每天早上5点上班,要干到很晚很晚。半年后,我回到家乡当了搬运工,搬的是水泥。我劲很大的,站在车子底下,车上人将水泥包梆梆的扔到我背上,两包水泥,我背着就走。后来母亲看见了,抱住我,大哭起来……低沉的女中音不紧不慢,瘪瘪的嘴唇忽闪忽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这个年轻的藏族歌手,仿佛在说着与己无关的别人故事。 停,停,停!刚刚惨不忍睹,又来个耳不忍闻,这不是雪上加霜,驼子背上加包,诚心要绝杀我这颗可怜的小心脏吗? 你看球,人家落花流水;你听歌,人家梆梆的扔水泥。都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我们来到世间,到底要经历怎样的不堪,才能不白活一回呢? 十来岁的小卓玛,那两包水泥,梆梆的就扔在她背上,她用的是“梆梆的”这个拟声词,掷地有声。虽然她是出土的笋子,呼呼长,有劲,但那里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县,与西藏江达县隔金沙江相望,平均海拔米。她一步一步地朝前走,一步一步,少一步也不行的。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大脑,强迫症似的想象着她背着那两包水泥步步惊心的样子。那个时候的小卓玛,脊背弯成了怎样的曲线,是大汗淋漓,还是气喘吁吁,或者兼而有之;她是一直往前走,不朝两边看,还是水泥灰迷了眼睛,睁不开,眼睛水啪啪的往下滴;她穿了怎样的衣衫,披了怎样的头巾,我们家乡码头上的水泥搬运工,都是五大三粗的男子汉,他们用一大块布从头顶披到背上,脸和水泥灰一个颜色,没鼻子没眼睛;她唱了劳动号子没有,如果唱了,用的是民族,通俗,还是美声,那声音是不是也像今天一样静若止水,又勾了人魂;她有没有想到来个自拍,再来一句“尼玛,累死宝宝了”,然后发到北京那个医院治疗白癜风最好北京看白癜风哪间医院权威
|
时间:2017/10/1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骑行川藏生命因经历而精彩
- 下一篇文章: 甘南看旅行达人如何玩转甘南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