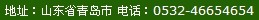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郭净,笔名azara(游方僧)。博士,现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致力于文化人类学、影像研究和社区教育,也是旅行者和写作者。 发表作品 著作:《朝圣者》,云南美术出版社年;《中国面具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心灵的面具》,上海三联书店年;《西藏山南桑耶寺多德大典》,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年;《去远方朝圣》,台湾大地出版公司年;《幻面》,深圳海天出版社年;《傩:驱鬼、逐疫、酬神》,香港三联书店年;《仙鹤到哪里落脚》(《去远方朝圣》简体字版),北京民族出版社年。 纪录片:《卡瓦格博》,《我心中的香格里拉——云南藏族拍摄的纪录片》(任制片人),云南音像出版社年。 8.杨朝桥调查 到底有哪些地区的藏族信仰这座神山,每年有多少人来朝拜,因没有见到切实的记载,我一直心存疑窦。并且,从人类学的角度,我更希望找到在文字之外的证据,用自己的眼睛作一个见证。但了解这样的事情并不容易,就我们接触的资料,国内学者对藏区朝山活动的实地研究还不多见。缺少由亲身经历编织而成的第一手证据,就少了实证的力量。当然,这对抱着虔诚信念的藏族不是个问题,就像《小王子》讲的,不需要用数字证明美的存在。可对于我,这依然难以释怀。 机缘终于来了。年,属羊的卡瓦格博适逢本命年,藏历新年之后,成群结队的朝圣者就出现在德钦的山路上。他们来自何处?有多少人?出于什么目的?属于哪个教派?等等问题萦绕心头。我虽然在6月做了一次外转经,但那时整天从早走到黑,连觉都不够睡,还不时地被高山反应、腹泻等毛病折磨,如何顾得上问这问那。不料到了10月份,香港的中国探险协会忽然交来一份差事,让我前往转山入口处的阳朝桥(又叫羊咱桥),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愿者做朝山人的问卷调查,方法是在阳朝桥这个必经之地设立接待站,为阿觉娃们提供茶水等服务,顺便让他们回答几个问题,以此作为转山调查统计的基础。 10月6日从昆明赶到德钦,便觉得气氛和6月大不相同。那时,转山的人多为本地藏族,街上并不怎么热闹。而此时班车一到站,就看见客运站的院子里熙来攘往,每趟去南边的车子都挤满了人,车顶堆满大大小小的包裹。我打扎西尼玛的手机,来接的却是斯郎伦布,说扎西和马骅带几个朋友转山去了。前天才完成第二次外转的仁钦老师刚回家,又领一伙人走了。县城各家旅馆都住满人,我找到一家熟悉的招待所,原先60元的房间涨到元。老板说早几天还贵,要元一间呢。 更麻烦的是车票。去车站,说票已卖完,让第二天早上8点来看。第二天一早赶去,说车还没来。等车来了,我又挤不进买票的人群,结果还是朋友帮忙,请站长留了一张下午2点30到阳朝桥的车票,我才得以动身。 车子3点才开,乘客都是转山的人,多来自西藏的昌都,也有几个刚转山归来,拿着竹杖的德钦藏族。司机是云岭乡日嘴村人,他边开车边聊天,说今年3至8月,转山的以云南藏族为主,到9、10月份天气凉一点,西藏、青海的牧民才赶来。他们多以村为单位结伴同行,一买车票就20-30张。客运站领导见此情况,把原来跑中甸、燕门、云岭的车子全部调到阳朝桥一线,才勉强应付了车票紧张的局面。乘客虽然多了,但他们上了山就不再回头,从西藏回老家,班车返回拉不到多少人。另外去阳朝桥的沿途都是滑坡和碎石路,非常危险,跑不了多久车子就坏了,所以司机赚不了几个钱。可为转山的人开车,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司机们并无怨言。 下午6点左右到阳朝桥。这是一座横跨澜沧江的铁索桥,建于年代。所有的朝山者都要在此过江,到附近的小庙“支信塘”拜祭,然后踏上转山的小路。香港中国探险协会看中这个地点,花钱加固了大桥的钢架,铺了新的木板,又在西岸的桥头建了一座三层藏式木楼,作为接待站,为朝圣者提供茶水和免费医疗服务,解答进山路线、住宿等问题,同时开展调查。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定期轮换,现在的几位是迪庆的学者张尼玛和张跃华,做饭并搞接待的是阿香、格绒拉姆,医生斯那次姆、次里拉姆,会说一点青海藏话的美国人柯涤凡,以及负责全盘工作的昆明人小钱。每一批人中还有从英国、法国、美国等地来的志愿者。接待站为调查人员提供免费吃住的条件,但睡觉只有一张床板,各人用自己的睡袋。 当天晚上就来了50多个青海玉树的阿觉娃,在屋外的石头地上睡了黑压压的一片。第二天10月8日,天气爽朗,转山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有西藏察隅的23人,那曲白嘎乡的6人,西藏比如县的6人,昌都的60人,丁青县1人,八宿县5人,察隅县的人,某村的60多人,青海玉树囊谦县50多人,玉树杂多县一车30多人。 在我参与这个项目之前,香港中国探险协会的志愿者们从6月就开始在这里收集转山人的资料。每天,都有一个人守在澜沧江西岸的桥头,一个一个数过桥的阿觉娃,多少人,什么性别,什么年龄,问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属于什么教派等等,用快速问卷的方法得到最基本的信息。也会在人群中邀请几个转山人进屋聊天,填写调查表。每个月底,都要做一次统计,下面是6-9月的转山人数:[1] 年6—9月卡瓦格博转山人数 月份 总数(人) 男人 (人) 女人 (人) 老人 (人) 成人 (人) 儿童 (人) 和尚 (人) 尼姑 (人) 马 (匹) 6 69 25 7 47 9 8 73 42 9 以上4个月的统计数字逐月增加,到我参加的10月份,转山的人数达到了一万多人。这之后的统计我没看到,但据该项目的组织者说,按照他们的调查数据,从公历年6月到年2月,到卡瓦格博外转和内转的朝圣者有10多万人次。我把调查表和笔记中的记录加以整理,发现他们主要来自以下地区: 云南:德钦县 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 西藏昌都地区:左贡县、芒康县、八宿县、贡觉县、察雅县、昌都县、类乌齐县、洛隆县、丁青县、江达县、边坝县 西藏那曲地区:索县、巴青县、比如县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玉树县、杂多县、称多县 四川省:德格县、石渠县、得荣县,乡城县 还有少量来自甘肃的藏族。 为了得到更详细的资料,我于10月23日到靠近西藏昌都地区的德钦县佛山乡了解情况。下午3点,我乘班车从升平镇出发,6点到达佛山。中巴车快到站时,见两辆西藏牌照的卡车停在路边,许多转经人在休息喝茶。天刚黑的时候,我到佛山派出所,民警扎史多吉介绍了有关情况,还让我查阅统计资料。据该派出所统计,从10月4日—12日,转山者所来的地区和人数如下(人数+人数=总数/车数): 西藏 类乌齐: 50+20+42+43+35+35+30+28+27+39+35+25+29=人/13车 昌都:6+42+40+32+37=人/5车 索县:42+37+25+35=人/4车 察隅:58+64=人/2车 八宿:16+36+35=87人/3车 芒康:15+10+13+37+5=80人/5车 左贡:30+10+14+17=71人/4车 洛隆:32+35=67人/2车 丁青:20+26=46人/2车 青海 囊谦:30+30+40+38+31+27+24=人/7车 杂多:36+31+28+25=人/4车 玉树:5+35=40人/2车 外转经的藏族,无论是哪个地区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同一个乡,甚至同一个村的形式前来转山。10月8日,我碰到西藏察隅县竹瓦根乡的一伙转山者,他们说全村的人,这次有60多人来外转,分为三组,其中一组有7家人,是: 尼巴家2人:一个男子(40多岁)和他的女儿斯那卓玛; 贡卡家4人:一个男子和他的女儿、姐姐、弟弟; 西空家5人:一个男子(30多岁)和妻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亚卡家4人:一个男子(60多岁)和两个女儿、一个孙女(4个月); 乌里孜家5人:一个男子(30多岁)和妻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卡拉家4人:两个兄弟和他们的妹妹、一个儿子; 吉尔家3人:夫妻和一个女儿。 我之所以重视以村为单位的朝圣者,是因为卡瓦格博的信仰不是单纯个人的行为,而是在群体交往和感染的背景下传播的。它主要是一种族群和社群的信仰。这些村落、地区乃至整个信仰区域的藏族必然有过长期的交流,既交换物产,也交流思想,甚至有过人的迁徙和文化的交融。 前前后后5个月的调查,第一次为我们揭示出了卡瓦格博朝圣者所分布的区域: 图66 如上图所示,卡瓦格博的朝圣者主要来自云南的德钦县,西藏昌都地区的左贡、芒康、八宿等11县,林芝地区的察隅县,那曲地区的索县、巴青县、比如县,青海的玉树州,四川甘孜的部分地区。其中,青海的囊谦县、西藏的类乌齐、左贡、芒康、察隅等县,是转山者来得最多的地方。 以上这些地区,在行政上分属于西藏和青海,但文化的共性和相互影响,并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如果以自然地理作为背景,便可以看出,朝拜卡瓦格博神山的藏族,主要来自澜沧江、怒江、金沙江三个流域覆盖的区域。其中,又以来自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人数最多。比如10月份转山人数最多的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的支流扎曲边;而西藏昌都地区的各县,都位于怒江—澜沧江,或澜沧江---金沙江流域。至于西藏那曲地区的索县、比如县、巴青县,都在该地区的东部,实际上位于怒江主流及其支流索曲旁。一个相反的证明是,分布于这三江(主要是澜沧江和怒江)之外的藏族,都没有以社区群体的方式来外转经。如云南迪庆的香格里拉县,离德钦并不远,但年,该县到卡瓦格博转山的都是个人,很少有以村为单位集体去的。 在上述地区,卡瓦格博一直都很有名,如察隅、左贡两县最主要的神山就是卡瓦格博,它们都位于这座神山的背面;来自比如县白嘎乡的欧珠和罗桑曲扎说,他们那里的藏族都听过老人讲卡瓦格博的故事,只是旧社会路不通,走不过来。知道今年是最好的羊年,他们三兄弟一起来了,7、8月去西藏的拉萨、日喀则、纳木错,又从比如到这里。索县亚拉镇的退休民办教师贡却单增(45岁)说,他没来之前,从老人和活佛那里都听说过卡瓦格博,正好同村一个叫朗珠的人三年前转过这座山,带回去一本仁钦多吉编著的《雪山圣地卡瓦格博》,便决定来了。因为路太远,车子坐不下(人多了要被罚款),每家只来一、两个人,其他人下一个羊年再来。当地5月至7月挖虫草,8月到亚拉镇参加赛马节,9月收割青稞,收完了才出来转山。 从青海杂多县来的格木南加(58岁)说,他们那里的人都知道这座神山,还有关于它的经书。每天早上烧香,都要念诵关于卡瓦格博的赞辞。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转过三次卡瓦格博,他本人此前也来过两次,一次是年,跟父母来转,那时没有车路,走了4个多月。一次是年,来了5个人,走一段路,坐一段车,花了3个月。这次他们共来了4辆东风车,每车30多人,他家一起来了11人,包括妻子和孩子。但现在脚痛得厉害,走不动,便出元找永支村的人代替他去转山。 在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覆盖的三江流域,还有其他的大小神山。然而,只有卡瓦格博成为该地区康巴藏族共同信仰的对象。在此地域之外,也有少数转山者来自拉萨等地,但以社区群体为单位前来外转朝圣的,均为三江流域、尤其是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藏族。从文化角度看,行政区域的分界,对信仰上的共同联系影响甚微。如德格县的藏族,在行政上属于四川管辖,但来自这个地区的转山者却表示:他们和西藏昌都仅隔一条金沙江,在文化上和昌都的藏族是一体的。又如囊谦县和石渠县的藏族,行政上分属青海省玉树州和四川省甘孜州,但他们都靠近澜沧江和金沙江的发源地,文化上有密切的联系。也因为同样的道理,其他地区如西藏山南地区、云南中甸等地的藏族,很少有以社区群体的方式来此山外转的习俗。 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分析,卡瓦格博信仰地域的藏族大部分生息在大江及其支流沿岸的河谷地带,以半农半牧为主要的生计手段。用《格萨尔王传》的词汇来描述,他们是“绒地”的藏族。 调查中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哪几个教派的人来外转卡瓦格博。结果发现,藏传佛教主要的教派如噶举、宁玛、格鲁等,都有大批信徒在羊年到卡瓦格博外转。如来自西藏类乌齐松卡乡的30人,和来自昌都县噶马乡的50人,都说自己是宁玛派的信仰者。原因是,藏地所有的神山,都是被莲花生大师降伏的,而莲花生就是西藏佛教的开创者,被藏族尊为他们的第一个喇嘛,也是宁玛派的创始人。由于这座山与莲花生的密切关系,卡瓦格博也成为宁玛派信奉的神山之一,成为该派信徒转经的对象。至于噶玛噶举的信徒,是年外转卡瓦格博人数最多的。其中又数来自青海囊谦县的人最多。我跟囊谦的转山人聊天,他们说,这个县噶举派多,自然朝拜卡瓦格博的人多罗。我查阅有关资料,才知道囊谦是青海噶举派的大本营。青海全省现有噶玛噶举派(包括黑帽和红帽两系)寺院34座,其中除了果洛的一座外,其他都在玉树藏族自治州,而玉树的噶举派33座寺院,有12座在囊谦。[2]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年的朝圣者队伍中还出现了相当多的苯教信仰者。此前只知道卡瓦格博在公元8世纪被莲花生大师降伏以前曾是苯教的神山,却没想到今天还有那么多苯教信众保持着对这座雪山的崇拜。10月份我见到的苯教转山者分别来自左贡县中林卡乡78人,左贡县乌雅乡三车50多人,察隅县扎拉区巴布村9人,察隅县竹瓦根乡60多人,那曲地区比如县白嘎乡的6人。他们的到来,说明卡瓦格博一直是澜沧江流域藏族佛教徒和苯教徒共同信仰的神山,这让我们对他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10月的调查,使我的眼光超越了德钦的范围,延伸到由横断山脉和三条大江所维系的广阔空间。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卡瓦格博是三江流域,尤其是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藏族群体所信奉的一座大神山,他覆盖了云南、西藏、青海的20多个县。我们可以把这座神山联系的“朝圣地域”,界定为“卡瓦格博信仰圈”。在这片地域内,每天都有几十万人焚香祈祷,念诵卡瓦格博的尊名: 供祭盖世圣尊卡格博, 奉养大德药王及眷属。 所有嘱咐教诲之功业, 皆以如意成就无阻碍, 祝愿雪山圣地及藏域, 芸芸众生幸福皆吉祥![3] 图67从神山下凡的第一位藏王。引自《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图说明镜》图25 图68四川甘孜竹庆一家牧民房子里挂的藏地圣地图,其中有主要的神山,包括卡瓦格博(白箭头处)。 图69云岭大峡谷里的八座宗。 图70八座宗图。仁钦多吉画 图71每年都有许多藏族到卡瓦格博朝圣。 [1]根据香港中国探险协会年卡瓦格博扎山人数统计表制作。 [2]参见莆文成《青海佛教史》第五章第四节,青海人民出版社年版。 [3]“圣地卡瓦格博焚烟供祭广文”,载《雪山圣地卡瓦格博》页。 点击扫描白癜风能治好不白癫风治疗方法
|
当前位置: 江达县 >学者田野雪山之书第十章信仰之源
时间:2018/9/2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第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
- 下一篇文章: 青春和生命铺就的天路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