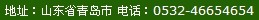|
阿扎宗遗址,在进藏路上,现位于嘉黎县范久辉摄漫漫进藏路文 杜冬对清代官员而言,驻藏路漫长艰险,无所不在的瘴气,神出鬼没的夹坝(强盗)、山洪、雪山,无不令人生畏。有一些官员百般推托,不肯前行,也有官员因为道路中断,在路上耽搁4年者(景纹,同治元年到同治四年)。昌都至江达(太昭),可能是驻藏路上最艰险的一段。常远制图乾隆年间成书的《西藏志》一书,记录了3条进藏的道路:自四川成都抵藏,前段也就是今天川藏南线为主;过金沙江后,到察雅、昌都、洛隆、江达到拉萨。乾隆时代藏区穆坪土司画像,进藏路上许多地段由土司管辖,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土司穿着装扮的模样。从打箭炉由霍尔迭草地至昌都,类乌齐进藏路线,前段和今日川藏北线大致一样,类乌齐之后走嘉黎、墨竹工卡。从西藏由木鲁乌苏一代到西宁的路线,即从拉萨向北,经林周到那曲,经过星宿海,日月山,抵达西宁。当年昌都的市井生活:夜静钟鸣,鸡唱犬吠,喧阒似一都会也。图为昌都老城的街巷。杜冬摄在这三条道路中,第一条道路显然是进藏的主要通道,时人指出,今天青藏线一带千里水草,人烟稀少,无法找到柴草、粮食的补给,也没有牲畜乌拉;所以整个清代,众多资料表明,进藏的官员、士兵、粮道、通信所走的是川藏南线。这条如今被称作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道路,高山大河密布,曾经却是艰险异常,逼仄难行,让我们跟随着《卫藏通志》的记录,走上这条进藏路。类乌齐人家。杜冬摄成都到打箭炉(康定)计程里(成都—双流—新津—邛州—雅安—荥经—清溪—冷碛—泸定—打箭炉)这段路在进藏之路中算是最好走的一段,人烟相对密集,然而即便如此,到了荥经之后,依然是“林木障翳,山谷阴森……沿沟直上,逼仄难行”,“蛮烟瘴雨,亦渐绘边檄之景矣”,已经给行人的心中投下了阴影。川藏路上飘劲寒冷的风更加让人有不能喘气的感觉。洛桑嘉措摄所幸打箭炉(康定)是塞外的繁华城市,当年的康定,自从康熙二十五年(年)准许进行边境贸易以来,已经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城镇。内地的物品,藏区的各种药材、土特产、黄金等都在此进行交易,其中最重要的货物自然是输送藏边的茶叶。康熙二十九年(年),康定每年的茶叶贸易达数万包。驻藏大臣进藏之路同时也是茶马古道,至今雅安的砖茶依然沿着这条道路行销整个藏区。杜冬摄史料记载,清代中叶,康定已经拥有了48家锅庄(办理货物往来的商业机构及货栈);嘉庆时,打箭炉每年商贸总交易额达每年一千八百余万两,可谓惊人。除了茶叶锅庄外,还有牛皮制造、缝茶业(为茶叶运输提供包装的行业),乾隆朝之后,康定人烟辐辏,市亦繁华,山海各货咸集,“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交易之盛,冠于西陲。”仅仅街道,就有营盆街、诸葛街、老陕街、明正街、茶店街、兴隆街、河西横街、安家锅庄巷子、小丹珍锅庄巷子、木家锅庄巷子、蜂窝街等,有四座桥梁横跨折多河上,可见康定城的繁华景象。打箭炉到里塘计程里进藏的茶马古道。插画黄日春(打箭炉—折多山—东俄洛—高尔寺山—雅江—剪子弯山—西俄洛—理塘)真正的高原道路从这里开始,离开康定,迎面而来的就是折多山,进藏路上的第一道雪山。“崇冈在望,峗嵲逼人,药瘴气候异常,令人气喘。”这是瘴气第一次出场,之后几乎无山无瘴。然而,作者站在折多山顶,也自生一股豪气,“自此一览山川之胜,蛮荒冰雪中,令人心摄”。高尔寺山:过大雪山二座,深林密箐,矗如玉立,人际罕逢。过雅砻江时,“蛮人以牛皮船渡,逐浪上下,望之如水中凫”。到了剪子弯山,人烟稀少之地,夹坝也开始出没。“此战路甚险远难行,且多夹坝。”西俄洛更向西,“林深谷邃,夹坝甚多”。理塘是又一重镇,“天寒多雨雪”,设有塘汛,且有正副土司二人管辖。理塘到巴塘计程里甘孜州理塘县是进藏路上的重要一站,图为理塘大寺长青春科尔寺,许多驻藏人员都记载了这座寺庙。杜冬摄(理塘—干海子尖—喇嘛丫—三坝塘—小巴冲—巴塘)这一段最令人痛苦的是高海拔带来的严寒和疲劳,人烟稀少,山路的艰险已经退居其次。“峻岭层岩,日色与雪光交灿”,“头塘寒风凛冽,冻绽肌肤,从此愈行愈冷”,“盘旋五次,大石森立,横梗道途”,“枯木参横,绝不闻鸟兽声”的记录比比皆是。道路如此艰险,以至于到达巴塘后,作者不禁感叹巴塘“沃野千里,水草环绕,日丽风和,佳境也”。巴塘到察木多(昌都)计程里昌都强巴林寺,寺主帕巴拉活佛与一些驻藏官员例如孙士毅等私交不错。杜冬摄(巴塘—竹巴笼(过金沙江)—莽里—江卡—石板沟—乍丫(察雅)—王卡—察木多)这一段路漫长,但不特别艰险,在金沙江河谷中穿行,气候尚属温和,人烟比较密集,除了有的路段“终年积雪,盛夏亦凉飙刺骨”外,夹坝(强盗)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文中“性桀骜,驾驭亦复不易”的记载比比皆是。道光年间,由于瞻对(新龙县)强盗纵横,导致从理塘至昌都的入藏正道竟然中断达4年之久。此外,作者还颇有研究精神地写道,在路上注意不要让马吃一种醉马草,马吃了就会如同喝醉,疲乏不能前进。拉里宗当年清军营房遗址。范久辉摄昌都,藏东的中心城市,清代进藏粮台和塘汛均以此为重要支撑点,雍正八年(年),清政府下令在两河交汇的台地上修建一座土城,“驻扎官兵,督理台站,游击一员,粮务一员,行营中军守备一员,把总一员”。昌都水草甘肥,土地亦异常肥沃,盛产萝卜、番薯,“列市廛,俨如都会”。 看当时人描写昌都,和不久前昌都老城区的景色差别不大,“所居背倚南山,碉房深邃,洞宇纡回,下临土埠,番民环集于其上。三面河坝,中隆起而顶平,幅员约计数里。石楼萧寺,高可凌云,彩能耀日。夜静钟鸣,鸡唱犬吠,喧阒似一都会也”。昌都强巴林寺的帕巴拉活佛,也与清代官员之间往来密切,乾隆时代督运军粮的总督孙士毅还有诗相赠。 察木多至拉里(嘉黎县)计程里驻藏路上的必经之地,边坝宗遗址。(察木多—俄罗桥—恩达—瓦合山—洛隆—硕般多(硕督)—边坝丹达山—甲贡—拉里)这段路或许是整段驻藏之路上最艰险,最为传奇的一段,往来的驻藏官员们无不浓墨重彩地描写瓦合山以及丹达山之险要。到达瓦合山前,道路已经“险异常,雪凌滑甚,且有瘴气”。瓦合山之险峻,令人胆寒,“高峻而百折,山上有海子,烟雾迷离,设望竿堆三百六十,合周天数,如大雪封山时,籍以为向导。过此,戒勿出声,违则冰雹骤至。山中鸟兽不栖,四时俱冷,逾百里无人烟”。山顶的湖泊中还有神怪,道光年间有官员记载,“海子中有独角兽,大如牛,过者见之以为祥瑞,蕃人谓之海神”。……(本文摘自《西藏人文地理》年7月刊,欲看完整版本,请在文末点击“阅读原文”订阅杂志哦,转载请注明出处及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ngdazx.com/jdxxw/6777.html |
当前位置: 江达县 >三百年前进藏路,清朝官员的人生畏途
时间:2021/3/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各界早新闻115周一语音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