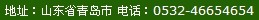|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在名人们的笔下,我们得以一窥南大岁月长河中的零星掠影。其中既有悠悠的书香,也有绵延的战火,有遗世的风骨,也有世俗的热闹。求学南大,既是在有形的土地上求知,也是在时间的河流里求索。其间学子心迹,或许正如余光中写的那样: 「在石头城的悠悠岁月,我长得很慢,像一只小蜗牛,纤弱而敏感的触须虽然也曾向四面试探,结果是只留下短短的一痕银迹。」 小新按 书香篇 余光中《金陵子弟江湖客》 ” 记得当时金陵大学的学生不多,我进的外文系尤其人少,一年级的新生竟然只有七位。有一次系里的黑人讲师请我们全班去大华戏院看电影,稀稀朗朗几个人上了街,全无浩荡之势。较熟的同学,现在只记得李夜光、江达灼、程极明、高文美、吕霞、戎逸伦六位。李夜光读的是教育系,江达灼是社会系,程极明是哲学系,高文美是心理系,后面两位才是外文系。其中李夜光戴眼镜,爱说笑,和我最熟。程极明富于理想,颇有口才,俨然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久便转学去了复旦大学,跟大家就少见面了。他仪表出众,很得高文美的青睐,两人显然比他人亲近。高文美人如其名,文静而秀美,是典型的上海小姐。她的父亲好像是南京的邮政局长,所以她家宽敞而有气派,我们这小圈子的读书会也就在她家举行。至于讨论的书,则不出当时大学生热中的名著译本,例如《约翰·克里斯多夫》、《冰岛渔夫》、《罗亭》、《安娜·卡列妮娜》之类。 吕霞和戎逸伦倒是外文系的同学。吕霞大方而亲切,常带笑容,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学者吕叔湘,在译界很受推崇。有了这样的父亲,也难怪吕霞谈吐如此斯文。 那时我相当内倾,甚至有点羞怯,不擅交际,朋友很少,常常感到寂寞,所以读书不但是正业,也是遣闷、消忧。书呢读得很杂,许多该读的经典都未曾读过,根本谈不上什么治学。因此当代文坛与学府的虚实,我并不很清楚,也没有像一般文艺青年那样设法去亲炙名流。倒是有一次读莫泊桑小说的英译本,书中把“断头台”误排成了quillotine,害我查遍了大字典都不见,乃写信去问我认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三个人:王云五、胡适、罗家伦。这种拼法他们当然也认不得,也许我写的地址不对,信根本没有到他们手里,总之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 盛静霞《中央大学师友轶事琐记》 ” 我到中大后,第一次上课,上的就是汪辟疆先生的“论诗”。吴梅先生创“潜社”,汪先生却创“雍社”。重阳节那天,叫来两部马车,中文系师生共乘,直达栖霞山。山多红枫,经霜弥艳。当时汪师偕诸生登一高阁,酒数巡,谈笑风生,命每人赋即景律诗一首,当场交卷,由先生修改后发还。我在中学读书时,虽也做过几首诗,但都是绝句,从未写过律诗,所以立即紧张起来。看看同系的学生,或倚栏凭眺,或在山径徘徊、沉吟,或一挥而就。我虽困窘,也只好勉强凑了一律缴上去。 回到宿舍,心里还是直打鼓。隔了两日,诗卷发还了,我一看,八句中竟有五句是先生写的,只留下我写的三句。当日有一位同学张迺香穿了一件浅黄色的汗衫,采了一大把红叶,抱上山来,我记得唐传奇《霍小玉传》中有黄衫客的故事,就写了“黄衫客拥赤云回”;又因山名栖霞,我名中亦有一“霞”字,似与此山有缘,末两句就写了:“最怜小字偏相似,疑是三生栖上来”。 我一看到这个结果就哭了起来,同寝室的汪仪璋问我为什么哭,我说:“诗做坏了,大部分都被先生删了,八句只剩下三句!”她却说:“我听说先生还表扬你哩!说你那句‘黄衫客拥赤云回’很形象,末两句虽然轻飘了些,也还可以。又说‘盛静霞是只未成形的小老虎,将来会大有作为的’”。我这才转悲为喜,从此努力写诗。 中文系蒋云从、盛静霞夫妇 人物篇 唐德刚《王赓武:天降大任》 ” 我在中央大学读书的那四个年头,实是我个人成熟后的生命中自觉学问最大、心情最好、身体最坏、生活最苦的四年,所以一直念念不忘。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我所遇见的当年“人间一坝”(沙坪坝)的旧伙伴,无不有此同感,因此彼此之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友情。但是我那时在伦敦碰到赓武,友情之外还兼具好奇之心,因为他是当年我母校的一位“南洋侨生”。而“南洋侨生”和当年中大的“朝鲜学生”、“边疆学生”等等,都是构成中央大学学术面貌多彩多姿之一环。 赓武在伦敦所给予我的印象是一个兼具中国国立大学学生潇洒底儒生气质,和端庄的英国绅士型的青年学者。他说的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和不带地方口音的中国普通话。他底马来语文也十分流畅;其他欧洲大陆的语文亦颇可使用。赓武也长得一表人材。风度翩翩,器宇非凡。看到赓武,就使我想起那时还在向我“口述历史”的顾维钧大法官来(顾氏时任职于海牙国际法庭)。我想此子也可做个顾维钧型的第一流中国外交家;也可做个第一流的中国“京师大学堂”的堂长。只因国族不幸,自相砍杀,把这种一流的人材胚子,都给浪费了;使他被赶到这儿来和一些老男、老女、教书先生们开他个什么“汉学会议”——我为赓武这样难得的专材可惜;并为国族有才而不能用,嗟叹无已。 叶兆言《黄侃:书生意气是狂狷》 ” 提到吴梅,不顺便聊聊黄侃先生,说不过去。南京大学中文系几大教授排行榜,无论怎么安排,不管如何布置,黄都是跳不过去的重要人物。说起宋词元曲,常讲吴梅当年;说起小学训诂,离不开黄侃。 黄侃视吴为“曲子相公”,吴梅称黄为“测字先生”,两个人内心深处,都不太买对方的账。最可笑的是两位老先生还打过架,黄脾气大,一言不合,先打一巴掌,吴不甘示弱,回一拳头。很多人将这事写进文章,都说喝了酒,打过就算,以后又和好如初。事实究竟如何,都是没见过的人在乱说。我们读书时,也曾听老师说过,老师又是听他们的老师八卦,说黄和吴心里有了别扭,不愿意再见面,安排课表只能想方设法,将上课时间错开。 据说程千帆先生临终,不能释怀的是未将老师黄侃的一本书整理出来。黄侃有许多学生,显然程很在乎这种师承关系。粉碎“四人帮”后,程能有机会回母校南大工作,也与几位幸存的黄侃弟子有关,他们是南大的洪诚、南师大的徐复、山东大学的殷孟伦。当时苏州有个语言学方面的会议,这几人私底下密谋,由洪诚向匡亚明校长推荐,最终促成了这件好事。 黄侃学问究竟如何,我的水平说不出所以然,只知道是“大得不得了”。当年上古代汉语,许惟贤老师喜欢把洪诚挂在嘴上,同时不忘强调洪是黄的得意门生。小学和训诂的正宗,说着说着,就离不开章黄门下。北师大的许嘉璐,官位达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也跟洪诚学过。我曾听他讲过课,说起训诂头头是道,可以想象,老师的老师的学问,有多厉害。 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弟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师大的徐复被称为活着的二号传人,一号是谁,始终没闹明白,反正轮到一个二号,学问已非同寻常。因为与徐的女公子熟悉,我与他老人家有过几次交往,印象中就是一本活字典,有什么字,有什么典故,向他请教,立刻给出答案,相当于电脑搜索。 黄侃门下学生回忆先师,异口同声佩服。不仅学生,黄的老师章太炎也赞不绝口,有一次,章翻阅闲书,读到“遇饮无人徼酒户,得钱随分付书坊”,觉得茫茫人海中,只有黄有此风味,立刻写成对联寄给他。很显然在章眼里,天下读书人多,爱读会读如黄者绝无仅有。可惜“一·二八”事变,为避祸,黄曾将藏书装了八卡车,送乡下暂存,没想到当地居民趁机盗窃,很多稀世珍品,就这么成筐论斤卖了。 徐有富《程千帆先生在南京大学》 ” 记得年9月18日,我们三位研究生第一次叩开了程先生的家门。初次见面,先生就强调:“你们的思想、学习、生活我都管。”谈话结束时,他还送给我们八字箴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我想这八个字正是程先生治学与为人的经验总结。程先生对我们的思想品格一直都很北京那个白癜风医院比较好北京那个医院白癜风最好
|
当前位置: 江达县 >客在金陵名人笔下的南大记忆
时间:2017/11/1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瑞安历史名人陈傅良被搬上荧屏微电影一代
- 下一篇文章: 春天里丹江醉春之旅君山旅行社丹江大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