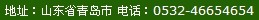|
治疗白癜风专家 http://m.39.net/pf/a_5941786.html D8:虔诚的白塔红墙 行程:江达-德格-炉霍,km在旅行的路上,早起总是一件好事,无论哪里的清晨都会让人神清气爽。尤其在川藏线上,每个清晨都有特别的风景。与我们一同早起的还有酒店老板娘可爱的儿子,可惜的是他早起是为了上学——也不是,他早就看惯了这样的风景。出江达县城不远,翻越矮拉山,下矮拉山就是川藏界河金沙江。矮拉山脚下,雾气笼罩着黄绿色的针叶林。横断山脉其实很多地方都分布有典型的寒温带针叶林,树种以云杉、冷杉、落叶松为主,下层是灌木和草甸,与喀纳斯和大兴安岭针叶林的树种其实很相似。有时我们会听到的泰加林,虽然也属于寒温带针叶林,但从定义上来说还是专指的北方针叶林带。矮拉山隧道已经通车,高度米,而山下的江达县海拔就有米,所以上矮拉山也只有很短的一段爬坡路段。隧道旁的盘山老路可以上到多米的公路垭口,还是传统的土路。垭口一定是比隧道的风光要好,但要花1个多小时爬上去,看这天气山顶也不会有雪景,还是把时间留给雀儿山吧,那里有终年不化的冰川。矮拉山隧道m,隧道外却是另一番景象,印证了川藏线上十里不同天的说法。矮拉山并不矮,从山两侧截然不同的天气就能看出来,金沙江巨大的水流量,在迎风坡面凝结了大量的雾气。国道上,很多路段也是没有联通信号的,而移动的卡基本是全程有信号。看看这一路的移动广告,在当地藏民的概念里,电话卡和中国移动就是一回事,不用懂什么是运营商。(移动的朋友,广告费还没到账)这里不是干热河谷,整个山坡都有草覆盖,有些牦牛还是会爬到山顶上。莫非是已经进化出了文斗的择偶观,谁爬得高谁更容易获得雌性的青睐?山下的岗托镇,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紧靠金沙江,还保留着当年战斗的桥头堡。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金沙江畔,过金沙江大桥就是四川德格县的管辖了。德格和昌都都属于康巴藏区的一部分,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民国时期的西康省包含了现在的四川甘孜州、昌都甚至林芝地区的一部分。在战乱的年代,西藏地方政权与民国政府在西康展开拉锯战,几经反复后以金沙江成为双方驻军前线,自此金江西岸的昌都地区便逐渐从事实上归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撤销西康省,才将昌都正式划入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中。德格虽然不大,在整个藏区的地位却是非常高,看看德格的Title吧。康巴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藏族传说中最有名的神话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乡;藏族三大文化中心之一,拥有中国最大的藏文印经院,另外两个是拉萨和甘肃夏河拉卜楞寺。上午十点多,进入德格县城。直奔德格印经院,因为这里中午是要关门休息的,得早点去。原以为印经院会比较安静,结果却出人意料。不大的印经院外面,已经有不少“转经”的人,大部分都是本地和其他地方的藏族信众,游客反倒不多。据漂亮的藏族导览小姑娘说,今天我们刚好遇上了旁边的更庆寺大法会,所以人非常多。这些转印经院的人,很多也是待会儿要去参加大法会的。印经院的墙角,放着一些刻着经文的石块,有些上面还画着青蛙、小狗这些图形。据说是有些藏族司机不小心撞死了小动物,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他们超度亡灵。德格印经院其实并不大,但是红墙高耸,自有一种庄严肃穆。德格地区的藏民基本都是信奉萨迦派,也就是花教,印经院的建筑风格也有着典型的花教寺院特点,院墙上方都有红白黑的花格装饰。萨迦派也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教派之一,创派时间比格鲁派更早。历史上有名的凉州会盟,就是由当时还在后藏地区的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端在凉州进行的会谈,从那时起西藏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纪录片《凉州会盟》,制作非常精良)。虽然地处萨迦派的信仰地区,德格印经院本身并不受教派限制,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经典兼容并蓄,否则也无法成为藏文化的传播中心了。印经院最早由第十二代德格土司主持建造,那时正是德格土司势力鼎盛的时期,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石渠、白玉、江达等地区。虽然几经战乱,政权更迭,即便在文革之中,印经院和院内的珍贵经版也在藏族人民的保护下完好地保存下来。德格印经院见证了土司制度的瓦解,也见证了军阀政权的更替,始终屹立在德格。文化这种无形的东西,在乱世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一直传承至今。这种力量,无法看见,却可以感知,有时它会出现在转经者虔诚的目光里,有时在雕版匠人沉稳的刀锋上。这种力量,叫做信仰。印经院内不让带相机,但是手机拍照又被允许,所以院内的照片都是出自iPhone7,暗光下的色彩还原度是个硬伤。我有点好奇,既然都是拍照,管理方又何必着相呢?德格印经院,各种各样的经版加起来有30余万块,不只有佛经,还包含了天文、历法、各类典籍、甚至是乐谱。由于原版极其珍贵,有些经版上甚至刻有德格土司专用的蝎子印章,大部分印刷用的经版都是经过复刻的版本。印制用的经版需要定期保养,重新刻画后,版面涂上酥油后进行晾晒,防虫防潮。经版分两种,朱砂版与墨版。最重要的典籍才能够用朱砂版进行印刷,其余的用墨版印刷。印刷时,两人配合,一人蘸墨涂在板上,另一人放纸后用滚动滚压,然后揭去纸张,快速判断是否合格,之后再重复上一轮动作。熟练的印刷匠人(严格说应该叫做工人,这是一个标准的工序流程,但在这里你很难把工业和印经院联系在一起),一天能印制好几千页。印制好的书页,需要挂在绳子上晾晒,待晾干后收起,由专门的人负责检查质量,合格品方能进行统一裁切,装订成书。印制板印制成册的经书何止千万,书中难免会有错误或者书写规范的问题,或者是长期印刷导致的印版损伤,这就需要专门的匠人来进行修正。需要修订的字迹在书页上用红笔描出,然后技艺高超的雕版师傅就会根据书页对印版进行修正,这不仅需要非常娴熟的技法,同时还要有很好的书法功底,算得上是印经院中的顶级工种。如果有比经版修复更加复杂的技艺,应该是唐卡画版的雕刻。之前在香格里拉唐卡画院介绍过,唐卡绘画是一种要求非常精细的技巧,最细的线条相当于于头发丝的粗细,极难绘制。那么要是在坚硬的木板上绘制唐卡呢?李寻欢能在木头上雕出林诗音的样貌,印经院里的雕版匠人应该能雕出她眼眸里的李寻欢。德格印经院的许多工序只能了解皮毛,藏文的经书内容就更不懂了,但依然沉浸在这古老的技艺中,带着一些对传承者的肃然起敬。我本想问,这些看起来极其辛苦的工序制造出来的经书,和印刷厂的机器印制出来的经书,对于藏族的读者来说有什么分别呢?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这个问题很幼稚。坐上火车去拉萨,和磕着长头去拉萨,有什么区别呢?11点半,德格印经院闭门休息。听闻旁边的更庆寺在举行大法会,去见识一下。印经院背后的山上有一些红色的房屋,围绕着一座金顶大殿。这些其实不是寺庙,而是一座五明佛学院(只要教授藏传佛教五明的都是五明佛学院,说到五明佛学院通常就会想到色达,只不过是因为色达的喇荣五明佛学院最出名),围绕佛学院的红色房屋都是僧舍。更庆寺的大殿之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信众,大殿之内更是无立身之地。法会是佛教的一种盛大仪式,但具体的仪式内容并不一定,一般来说都会有说法讲经,设斋,受戒等流程。无论法会内容如何,对于信佛之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庄重而神圣的盛会。人群之中,围坐了一圈僧人。比较奇怪的是,更庆寺为萨迦派寺庙,这里的信众也基本都是信仰萨迦派的,按说应该是戴红色僧帽,不知为何戴的是格鲁派的黄色帽子。法会正式开始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半,还有接近两个小时。留下来应该也是看个热闹,便知趣地离开了。德格地处甘孜州的边界,县城几乎全是藏族人。大橙子这几天对藏餐的兴致很浓,想去试试这里原汁原味的藏餐,我就没什么胃口了,因为基本都知道有些什么吃的。她所喜欢的,大概是香格里拉古城里的那种改良后的藏餐。果然,在走进一家正宗藏餐馆之后,看了看其他桌上的硬核藏餐,加之无法语言交流,便劝退了,最后在路边吃了一碗炒饭完事。继续上路,沿途依旧是浓厚的佛教气息。随处可见白塔与红墙,大大小小的玛尼堆更是不绝于路,即便在山上,大块的石头上面也画满了彩色的佛像,刻着六字箴言。路边的村子里,也有许多身着红袍的僧侣与信徒。向着川藏第一高山雀儿山进发。上山不久,视野里就出现了雀儿山独特的尖利山石,簇拥着一片白色冰川。雀儿山位于横断山脉中最宽阔的沙鲁里山脉北段,主峰米,曾经的公路垭口海拔米,为川藏南北两线最高点。十八军进藏时,一面修建川藏公路一面进军,筑路过程中牺牲的官兵与民众却远远高于战斗减员,其中最难修筑的路段包括二郎山、怒江山,还有就是这座雀儿山。川藏线筑路总共牺牲的英烈超过人,可以说川藏线每个里程碑下面就是一个烈士的忠骨,而雀儿山上每公里牺牲的战士甚至达到了7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军当年能够修筑起川藏公路进军西藏,与清朝对西藏地区的长久经营是分不开的。西藏自元朝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但明朝两百多年实际上是没有对西藏进行管理的,也没有驻军。直到改朝换代后,清朝政府对西藏的政教领袖进行册封,并在雍正年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驻军西藏,才开始对西藏的实质管理,一直持续到晚清。在清朝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还平定了巴塘叛乱,进行土司制度的改革。大部分人都知道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成为了腐败衰亡的晚清黑暗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其实在国力衰竭之时,仍未放弃同在边陲的西藏,这一段也应该得到历史公允的评价。雀儿山隧道在前几年已经通车,全长12公里,高度超过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特长公路隧道。在隧道口,确认了一下大橙子没有高反,便按照原计划调转方向,驶上老的山路。其实当时心里略微犹豫了一瞬间,不再养护的老路是否危险?山顶有没有大雪?无人机会不会坠毁在垭口?但最后一个问题打消了这些顾虑——不上去看看会不会遗憾?只走了不到米,路就被拦起来了,还不是几个石头和塑料桩,而是一大方土。没办法了,只能乖乖地走隧道。站在坡上,看见一段老路消失在彩色的树林里,还是有些失望。这样的土路,如果不加以维护,退化的速度是很快的,多年以后可能就完全湮没在山林之中了。土堆旁,有一座张福林烈士陵园,陵园中的碑上刻着这位战士的短暂一生。在修筑雀儿山公路时,身为班长的张福林带领士兵进行爆破,遭遇大石塌方,壮烈牺牲,年仅26岁。张福林只是许多为川藏公路献出生命的战士之一,雀儿山隧道口已经在修建关于十八军筑路的纪念馆,落成之后也会有更多当年筑路的故事被展现给今人。新的纪念馆当然有更好的宣传作用,而老路边的这座陵园,却可以让烈士英魂长伴公路,夜枕青山。对于长眠于此的战士来说,永远守着这条心爱的川藏公路,就是最好的归宿。我在碑前伫立了一分钟,算是后人对先烈的一种缅怀吧。收拾心绪,继续上路,规规矩矩地按照限速通过隧道,十二公里长的隧道走了接近20分钟。隧道另一端,冰川的融水汇成一条溪流,通往山下的玉隆拉措。玉隆拉措还有个名字叫做新路海,是当年筑路的部队起的,可以想像当年进藏的官兵看到这个湖的时候,是冰天雪地里少有的慰藉吧。自驾游时,风景是否美,很大程度依赖于期望值有多高。关于新路海,我只是告诉大橙子下山会有一块湖,没有说这是川藏北线上一处很有名的风景。所以此时站在路旁眺望这片湖,怎么看,怎么好看。因为没有上到雀儿山垭口,无人机的电池现在还饱和着,就在玉隆拉措放肆飞吧,余下的路程也没有太多的放飞机会了。到玉隆拉措的湖边看着近,真要走还是要不少时间,这里海拔也有米。远观一番之后,便又踏上旅途。雀儿山的冰川是很有名的风景,上山之后其实也只看见一点点,难道真的是因为今年太过暖和,冰雪的补给不够了?以为雀儿山的旅程已经结束,往山下走的时候,却从后视镜中瞥见了一座壮观的冰川。此时微单狗头的短板就暴露出来了,55mm的焦段完全无法还原冰川的壮观,身临其境其实是非常震撼的。下山后往甘孜县,直到今天的目的地炉霍,都是一马平川的草原公路。这样的草原,在川藏线已经司空见惯。现在是下午四点,离目的地还有公里路程,按这样的路况,应该两个小时就能到。但是甘孜的交警并没有成人之美,这段草原公路有太多区间测速,一段接着一段。区间测速的蛋疼之前就已经说过,只能在途中找风景好的地方消耗时间。然而尽管是一路的草原风光,区间测速的终点却往往设在景色最差的地方,只能停车学习,让人毫无脾气。甘孜到炉霍的路上,途经一片百里青稞画廊。看上去若是在深秋季节,满原金黄,应该也是很美的风景。现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就很普通了,强烈的阳光还有些逆光,整个青稞画廊都失去了色彩。阳光强烈到什么程度呢?照在绿色树叶的背面,我竟以为是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还在想什么树能这么神奇,枯叶与花朵共一树。爬上一座小山丘,山谷中出现了小半截彩虹,很快就没入云层中。在川西的草原上,彩虹是常见的风景,常常会出现完整的虹桥划过草原的景观,这在内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今年上半年成都倒出现过一次,那时朋友圈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地震和下雪。其实从雀儿山下来之后,我心里还藏着一处风景。很小的时候,到过一次川藏北线,位置在甘孜与炉霍之间,我记得那天早上翻上一座山丘之后,有一排林立的雪峰横亘在眼前。那排雪山给我的印象太过深刻,所以我一直记得那个地方叫做洛戈梁子。直到炉霍,我也没有找到印象中的那边山,也没有见到有洛戈梁子的路牌,难道是二十多年的记忆将那排普通的雪山幻化了吗?直到写游记到这里,整理照片时我才发现,我相机里竟然有这座山。是在一个弯角处,鬼使神差地下车回头拍了一张照片,在相机屏幕上完全看不清细节。后来又在地图上进行了比对,确认拍照的地方就是在洛戈梁子,而远处一字排开的雪山,就是当年看到的那一座,只不过记忆确实将它加工得过于巍峨了。晚上7点抵达炉霍,这座印象中破旧的小县城,没想到竟发展得这么好了。县城街道整洁,建筑有序,色彩统一,酒店餐馆也非常多。自从雅康高速通车以后,越来越多的自驾游客将第一站安排在炉霍,极大地带动了县城旅游配套的发展。今天入住的酒店是此行最佳住宿,窗户正对山坡的寿灵寺,号称禅景房。晚上在一家叫做木雅藏餐的餐厅,终于满足了大橙子想吃藏餐的心愿。牛肉汤、牛肉饼、凉拌蘑菇,其实跟藏餐没多大关系,基本都是家常口味,连酥油茶喝起来都格外清淡。基本确定明天要改道,晚上收到老刘发的一条消息说明晚折多山有暴雪。汶马高速断道,熊猫大道封路,川西返程全都挤到上,想必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为了不让旅行最后一天变成毫无乐趣的赶路,我跟大橙子说我们还是一路走一路玩,随遇而安。就是带着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我与贡嘎擦肩而过,让这座山在心里又变得更痒了一些。(未完待续,敬请期待《走,去横断山河》(十):归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ngdazx.com/jdtq/7372.html |
当前位置: 江达县 >走,去横断山河九虔诚的白塔红墙
时间:2021/4/1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跨越70年的ldquo红色rdqu
- 下一篇文章: 林芝观山季选一条最好的线路,看一座最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