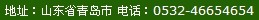|
白癫风能好吗 https://m-mip.39.net/news/mipso_6288655.html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研究 刘玉皑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摘要: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是以茶马古道西藏段为纽带,将多个相毗连的具有相关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城镇彼此连接而形成的线状城镇分布区域。古道沿线城镇拥有丰富且内涵深厚的相关历史文化遗产,通过整体性、保护性和多元一体化的廊道建设,对茶马古道西藏段城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城镇可持续协同发展以及“一带一路”战略下“南亚大通道”的建设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 “历史文化名城廊道”指多个毗连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城镇彼此连接形成的城市带,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的“线性文化遗产(LinealorSerialCulturalHeritages)”概念有相似性。“线性文化遗产”是由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以某种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移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并赋予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1]同样由历史文化遗产构成的带状区域,后者强调区域内的文化遗产,前者以区域内拥有历史文化遗产的城镇为链接要素。 与“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等点状文化遗产区域相比,“名城(镇村)廊道”涵盖更为广阔的线状、链状或带状历史文化遗产区域,不仅覆盖了更多种类的人类文化遗产,更反映了不同区域之间人类的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 目前西藏地区的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皆分布在茶马古道西藏段沿线,这些城镇几乎都拥有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以茶马古道为纽带建设名城(镇村)廊道,呈现茶马古道在西藏的发展历史,能够更深入地挖掘和展示古道西藏段历史文化遗产的内蕴,更有效地实现对西藏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保护与开发,实现名城(镇村)间的协同发展,是西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推进“南亚大通道”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茶马古道西藏段的历史“茶马古道”是当代学者提出的概念,指自中古至近代时期,我国中央政府与西部边区游牧族群进行以茶换马贸易的通道。这条以骡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贸易路线,是历史上连接陕、甘、青、滇、川与西藏地区,并延伸至南亚、东南亚各国的重要交通路线和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历史悠久,它的形成是与我国藏区人民的饮茶需求和中原王朝战马需求的双重推动下促成的。青藏高原属高寒地区,在这里生存的藏族民众以糌粑、奶制品、酥油、牛羊肉等高热量的脂肪类食物为主食,茶叶作为分解脂肪、防止燥热的辅助饮品,受到藏族人民的喜爱。由于藏区不产茶,而中原王朝需要牧区畜养的优秀战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马贸易应运而生。唐玄宗时期,“茶马互市”出现,开启了藏区与中原地区茶马贸易之始。伴随茶马互市的开展,藏区的马匹与内地的茶叶南来北往、流动不息,逐渐形成茶马古道。根据学者的研究,历史上连接我国汉茶和藏马的“茶马古道”路线主要有青藏道、川藏道和滇藏道三条。 (一)青藏道 唐贞观十五年(年)文成公主进藏,茶作为陪嫁之物传入藏区。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了茶和茶碗,能够区分汉地茶叶的种类和好坏。[2]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唐准“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3]固定的马土贸易路线逐渐形成。此时,吐蕃饮茶者多为上层贵族和僧侣,对汉茶的需求量还不大,唐仍以丝绸之类的日用物品为大宗与吐蕃市马。这条自长安始,至逻些(拉萨)终的路线,基本上沿“唐蕃古道”前行,后来被称为茶马古道青藏道,根据《青海省志·唐蕃古道志》记载,该路线大致为: 京兆府长安城(今陕西西安)→凤翔府(今陕西凤翔)→陇州(今陕西陇县)→秦州(今甘肃天水)→渭州(今甘肃陇西)→临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鄯州(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临蕃城(今青海西宁镇海堡)→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大方台)→赤岭(今日月山,青海湟源西南)→树墩城(今青海察罕城)→莫离驿(今青海恰卜恰/共和东坝)→大非川(今青海大水河/切吉草原)→那禄驿(今青海大河坝/鄂拉川)→众龙驿(今青海称多县清河乡)→藤桥→列驿(今青海玉树结隆乡)→婆驿(今青海玉树杂多野云松多)→悉诺罗驿(今青海当曲以北加力曲)→鹘莽驿(唐古拉山查午拉山口)→野马驿(今西藏聂荣县白雄)→阁川驿(今西藏那曲北部)→蛤不烂驿(今西藏桑雄)→突录济驿(今西藏桑雄桥以北)→农歌驿(今西藏羊八井)→逻娑城(今西藏拉萨)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所易马匹主要产自青海一带,川茶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青海并经由青藏道入藏。至清代,中央政府修筑入藏驿站,以唐蕃古道为基础的青藏驿道在年被启用,但因气候严寒、水草缺乏,后被迫撤去台站,官商改走康藏驿道,经打箭炉(四川康定)入藏。 (二)川藏道 历史上,四川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宋神宗熙宁七年(年),四川成都设置茶司,秦州设买马司,分别管理买卖四川茶叶与藏族马匹事宜(后茶场、买马二司合并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互市事宜),标志着中央政府正式与藏区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川藏茶马古道分南、北两路。 北线:成都→都江堰→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那曲→当雄→拉萨 南线:雅安→康定→里塘→巴塘→芒康→昌都→洛隆→嘉黎→工布江达→墨竹工卡→德庆→拉萨→日喀则[4] (三)滇藏道 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茶树品种资源,西双版纳、普洱等地一直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之一,也是历史上藏区茶叶的主要来源地。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向外扩张,与南诏开展包括茶马贸易在内的商贸交流活动。宋熙宁时,在云南北胜州(今丽江永胜县)设茶马互市,元代在永宁(今丽江宁蒗县)设茶马市场。自宋代至清康熙年间,茶马互市滇藏道自云南南部产茶区西双版纳、普洱和北部茶叶集散地北胜州、永宁,北上经大理、怒江、迪庆等地进入西藏至拉萨。滇藏道入藏后的路线分为南北两线,具体路线如下: 北线:芒康→昌都→类乌齐→洛隆→边坝→嘉黎→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拉萨 南线:察隅→然乌→波密→林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拉萨 滇藏道至昌都后,还有一条分支线路:类乌齐→丁青→巴青→那曲→当雄→羊八井→拉萨 通过以上青藏道(唐蕃古道)、川藏道和滇藏道茶马运输线路,陕、川、滇茶区的茶叶等贸易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地区,满足藏区人民日用所需。其中,从川、滇输入的茶叶,在到达西藏拉萨后继续西行,经亚东、聂拉木出口,进入尼泊尔、印度境内,形成横跨西藏、连接诸多城镇的庞大交通网络。 综合以上线路,茶马古道西藏段的基本路线大致可分为由内地至拉萨的北、中、南三线和由拉萨至尼泊尔、印度的西线,共四条线路: 北线:江达→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那曲→当雄→羊八井→拉萨 中线:昌都→洛隆→边坝→嘉黎→工布江达→墨竹工卡→拉萨 南线:芒康→左贡→然乌→波密→林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拉萨(或芒康→左贡→然乌→波密→林芝→泽当→江孜) 西线:拉萨→江孜→康马→帕里→亚东→至印度;拉萨→日喀则→拉孜→定日→聂拉木→至尼泊尔 图1:茶马古道西藏段主要线路 二、西藏茶马古道沿线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作为汉茶的输入地、蕃马的输出地和中国内地与南亚、东南亚贸易交往的中转地,茶马古道西藏段无疑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地区。茶马古道的贯通,不仅满足了西藏地区藏族人民的生活所需,更留下了茶马古道西藏段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前者主要是指道路、桥梁、驿站等建筑文化遗产和与茶叶相关的历史遗留物;后者包括古道商贸文化及其商贸文化所体现的古代民族交流融合、近代爱国主义等精神文化遗产。从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的发现来看,西藏段现存有关茶马古道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为: 道路。茶马古道道路本身是古道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载体,这些由马帮踏出的道路简易而艰险,却成为藏区与周邻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动脉,又加自主线纵横延伸出来的诸多支线,茶马古道西藏段形成庞大的古代区域交通网络。 溜索与桥梁。由川、滇入藏的茶马古道,需要横渡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跨越西藏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溜索和桥梁成为连接古道必不可少的要件。“溜索”是藏区最惊险的过江方式,在没有桥梁的江面上,马帮、骡马牲口和货物都用溜索的方式过江,稍不注意便可能葬身激流之中。桥梁在古代西藏屈指可数,一般修建在人口集中的城镇附近。马帮入藏后,为行走方便及彰显实力,曾在古道沿线一些重要城镇修建桥梁,20世纪初昌都城周的西藏桥、云南桥、四川桥便是分别由西藏、云南、四川的马帮投资修建的。修桥的同时,马帮也修建庙宇,以祈求桥梁永固,路途平安。[4] 寺院。茶马古道不仅是商业通道,也是来往此间的藏传佛教信徒们的朝圣之路。由于朝圣路途险远,信徒或喇嘛前往拉萨往往追随马帮共行,藏传佛教文化也随之渗透到马帮所及的古道沿线各地,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成为古道马帮商队及藏传佛教信徒们的歇脚地和精神驿站。除寺院外,难以计数的玛尼堆、转经房肃穆地静立在古道沿线的山梁、路口和村头。川滇与西藏交界区域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反映出古道多文化、多宗教交往的历史,如左贡县碧土乡寺庙废墟中,半坍塌的大殿形态便为汉、白、纳西族民居所有的四合院结构。[5]藏传佛教寺院也直接参与西藏茶马古道沿线的商贸活动。历史上,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财富,控制藏区的农牧业和商业等行业,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20世纪50年代以前昌都强巴林寺的商业机构从寺院、活佛到寺内各札仓多达9家,专门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员有49名,拥有商业资本多万大洋,川茶、毛料等商品是强巴林寺主要经营门类。古道沿线的其他寺院,也往往直接与停驻休息在寺院中的马帮商队进行交易,以食宿、马料或货币换取砖茶,再转卖与周边藏族百姓。 茶馆。西藏地区拉萨、日喀则、林芝、昌都等人口集中的城市分布着众多茶馆,甚至在城镇之外的茶马古道沿途路边也开设有小茶馆。甜茶馆是西藏城镇的文化特色之一,饮甜茶的习惯则是藏民受印度、尼泊尔影响,甜茶正是沿着茶马古道西藏段的西线,由马帮商人们驮运到古道沿线各个城镇的。甜茶馆是普通藏族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的聊天休闲场所,记录着藏民的“慢生活”;同时,茶馆也是信息最集中、传播最快的地方,在拉萨,“甜茶馆消息”就是小道消息的代名词。 相对于目前所知数量、种类较少的物质文化遗产,西藏茶马古道沿线城镇所蕴含的相关精神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意义深远,包括饮茶文化遗产、商业贸易文化遗产、爱国主义文化遗产、民族交流文化遗产等形式。 饮茶文化遗产。西藏地区的饮茶习俗最早是在僧侣间流行起来的,时至今日,藏传佛教寺院僧侣的生活也与茶密不可分,每日早、中、晚三次诵经礼佛活动后都要集体饮茶,饮茶期间还需遵守相应的礼节、规则;此外,僧侣们在念经打坐的闲暇也私下饮茶。巨大的茶叶需求,产生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收茶节日,即“滚芒嘉”,由信徒们给寺院布施茶叶;部分藏传佛教寺院还举行大型茶会,如拉萨大昭寺过去举行传召大法会时,为近3万名僧侣供茶饮用。[6]除僧侣外,藏族老百姓也普遍饮茶,形成了民间独特的茶具文化,如多种形制特点的茶碗文化。此外,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多与茶相联系,如将茶叶和经书等一起装进新塑成的佛像内,佛像会更有灵气;重要的节日期间,在神龛前供奉质量上乘的茶砖;等等。 商业贸易文化遗产。西藏茶马古道名城廊道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显著地表现在古道城镇承载的贸易文化遗产方面,如商号文化、马帮文化等。古道上最著名的藏族商号“邦达昌”,是民国初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于昌都芒康的邦达·阳佩、邦达·热嘎、邦达·多吉三兄弟在西藏区内外、国内外商业活动的总称。三兄弟分别坐镇拉萨、昌都和印度噶伦堡,商号的分支机构几乎遍布古道沿线的重要城镇,商号资本雄厚,左右当时藏区的茶马贸易。20世纪40年代,邦达家族每年从川、滇采购砖茶3.5万包、尖茶5.1万包,从藏北收购羊毛14万公斤,从事藏区和内地之间的茶马贸易,其贸易范围甚至远至印度、尼泊尔等国,商业实力在当时西藏盛极一时。[6]抗日战争时期,邦达昌以其骡马商队开辟陆地国际运输线,有力地支援了大后方,功绩卓越。与商号文化齐肩而立的是古道马帮文化。马帮即包括赶马人、骡马、牦牛和货物组成的茶马古道运货队伍,可以说,茶马古道就是由马帮一步一步踩出来的。马帮内部严密的组织、营运管理制度和特殊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独特的茶马古道马帮文化。 爱国主义文化遗产。鸦片战争后,英国试图以印茶取代行销西藏的华茶,以垄断西藏政治与经济。当时,保护川茶、抵制印茶销藏,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茶销藏。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清廷官员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倾销印茶。其后清廷在四川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这一时期通过茶马古道入藏的川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年,日本入侵缅甸,中国西南国际交通道路——藏缅公路被截断,由四川康定和云南丽江入藏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当时在我国西南地区工作的俄国人顾彼得如此描述茶马古道上的这段盛景:“这场‘马帮运输’曾使用了八千匹骡马和两万头牦牛,几乎每周都有长途马帮到达丽江。”[7]年,滇西多名赶马人和近匹骡马组成马帮,沿茶马古道滇藏道将20万公斤粮食运到西藏,这次运粮援藏行动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8] 民族交流文化遗产。古道往来贸易的藏族、纳西族及回族、汉族等,彼此间影响,形成古道沿线城镇独特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西藏芒康的盐井,明代时曾是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占领的地方,当地的纳西族在与藏族和往来古道的“藏客”不断的交往融合中,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说讲藏语,服饰装束也藏化了;东巴教、藏传佛教甚至是天主教在此形成了多元文化汇聚、和谐共存的形貌。行走古道的马帮商人也为藏区藏族传统文化加入了异地文化的因子,西藏左贡县加朗村藏族村民世代传唱的歌曲便有苍山洱海的远景。 三、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的建设上述茶马古道西藏段多样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多数是以古道沿线城镇、村落为载体保存和展现的。挖掘、研究古道沿线城镇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以茶马古道为纽带,建设古道名城廊道,是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举措。 (一)古道名城廊道的建设基础 历史上,昌都、江达、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等城镇皆是西藏地区茶马贸易重要的交易地点和中转站,这些城镇的发展与茶马贸易密不可分。在以上城镇中,江孜、拉萨、日喀则已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周边的萨迦镇、昌珠镇、帮兴村、吞达村、错高村则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表1:茶马古道西藏段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目前西藏自治区被列为国家名城(镇村)的城镇主要以拉萨市、日喀则市为中心,分布在茶马古道西藏段中西部的沿线一带,这是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建设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基础。 (二)古道名城廊道的建设原则 1.时空二维视角、整体协调把握 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的建设,即以茶马古道为纽带,构建沿线名城(镇村)毗连的线状通道。该廊道并非名城(镇村)的简单连接或集聚,而是由记录和展示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要素的城镇在特定空间内的有机整合。因此整体性原则是古道名城廊道建设的首要原则。 古道名城廊道是一个整体系统,需要以整体的视角、以全局长远发展的眼光进行建设规划。一方面,制定纵向时间上有节奏的建设步骤,先架构、后充实,分清主次、按部就班;另一方面,注意廊道整体规划与相关城镇发展规划的横向对接,兼顾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实现协同发展。 就目前情况来看,西藏茶马古道沿线的名城(镇村)虽然都分布在古道沿线,但城镇数量极少,且主要分布在古道沿线西段。因此,增加古道沿线中段和东段名城(镇村)的数量,构建廊道框架,是古道名城廊道建设的首要工作。此区间内,古道路线长、沿途城镇多,但大多数是人口较少的小城镇或村落,因此,中段和东段框架的建设重点为:筛选古道沿线各段有代表性的重要城市,调查古道沿线各段存留相关历史文化遗产的典型村镇。 综合考虑西藏茶马古道的发展历史和当前西藏城镇发展的现状,古道东段可选昌都、芒康,中部可选林芝与工布江达,作为廊道名城(镇村)的备选城镇。在完成框架建构后,可继续充实廊道的名城(镇村)因子,如中段的那曲,西段的亚东、帕里宗,东段的类乌齐、邦达、江达等,都是古道沿线较有特色的城镇。 2.文化保护为先、城镇协同发展 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建设的目的具有双重性:其一,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保护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其二,以茶马古道为纽带,促进西藏城镇的可持续协同发展。两个目的皆强调了“保护性发展”的原则。在古道名城廊道的建设中,保护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即尊重古道沿线城镇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不破坏、篡改或随意添加信息;注意城镇建设规划与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实现城镇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茶马古道不仅是商贸交通要道,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包括伴随茶马古道而生的道路、桥梁、驿站等物质文化遗存和商贸文化、马帮文化、饮茶文化、爱国主义、民族融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木霁弘等研究者指出,茶马古道一旦遭受破坏,将给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带来巨大损失。今天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令人堪忧,道路的石板有的被人撬走移作它用,有的道路被柏油、沥青路面覆盖,有的则因长期废弃而湮没在碎石杂草之中;过江的溜索、木桥朽烂,驿站倒塌,玛尼堆散落,茶馆关闭……茶马古道的痕迹正日渐消失。几队马帮的偶尔行进,或以古道为旗号的节日汇演,无法根本性地改变上述局面。 “历史文化名城(镇村)”本身强调对城镇具有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其免受破坏,因此,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的文化遗产发展之路,是实现在发展中保护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这一城镇廊道建设的理念对藏区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保护意义。西藏地区生态系统脆弱,人口承载力较低,无法沿袭中东部地区城市的工业、商业化发展道路,但城镇化的发展又是中国城镇发展和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建设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便是综合考虑西藏城镇化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上佳选择。 3.古道文化为体、多元特色突出 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建设涉及古道沿途多个城镇的有机整合,廊道总体上具有茶马古道西藏段历史文化特色,体现风格和要素的一体化原则。同时,西藏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构成要素又具有多元性,包括形态不一的物质文化遗存和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因子。在建设古道名城廊道时,还应注意在一体化的原则下,
|
当前位置: 江达县 >西藏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名城廊道研究
时间:2020/12/1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龙口市江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工会组织员工旅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