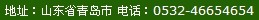|
引子 纪念一位老人的离去。 最近一次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是他为台湾教科书大幅度删减文言文比例而痛声疾呼。让我惊诧这位老人枯瘦的血管里面居然蕴藏着火山一般的力量。是的,哲人菩萨低眉,更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遥想13年前,我与这位老人的邂逅。之前我看到老人在《收获》上写的文章《金陵子弟江湖客》,结尾这样写到:"我走进阴深的大阅览厅,一步,就跨回了五十年前。空厅无人,只留下一排排走不掉的红木靠背椅子,仍守住又长又厚实的红漆老桌,朝代换了,世纪改了,这满厅摆设的阵势却仍然天长地久,叫做金陵。我抽出一张椅子来,以肘支桌,坐了一会。舒曼的《梦幻曲》弥漫在冷寂的空间,隐隐可闻。我相信,若是我一个人来,只要在这被祟的空厅上坐得够久,李夜光、高文美、江达灼那一伙同学就会结束半世纪捉迷藏的游戏,哇的一声,从隐身处一起跳出来迎我。" 江达灼是休宁中学的老校长,我看到文章之后,多方辗转,使得两位老人通上跨越世纪和海峡的电话,我还兴奋地写下文章《金陵子弟来相问》。后来,老人来北京参加新京报文学盛典。老人看着稚嫩的我,写下鼓励的文字“乐见江达灼老同学,有如此佳弟子,乃双重的喜悦。” 仍然记得老人当时演讲的结尾:“冥冥之中,我似乎看见仓颉在点头,女娲在回眸,严肃的韩文公在向我开言微笑。苏轼说:在岛上的文字,最后总归要传回中原。”后来,我到了东坡翁写这首诗的地方,海南澄迈驿通潮阁,我在蕉风椰雨里瞭望大陆的远山,仿佛听见东坡当年的吟唱:“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那不就是余光中老人的心声吗?海岛上的文字,终归要回到中原。余光中先生的离去,更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代人的离去,大陆时期的中央大学校友又走了一位。缅怀余光中先生。祝先生魂归故乡。 金陵故友来相问 ●文/吴子桐 壹 那个冬日的午后,我在北大图书馆暖暖的日光里,翻阅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新来的一期中有余光中先生的散文:《金陵子弟江湖客》。 余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这些后辈晚生是佩服得紧的。正像梁实秋先生评价余先生是:“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我十几岁时候读到先生的那首《乡愁》,当下里颇为喜欢,用我那稚嫩的笔迹,工工整整地誊抄在我的“读书笔记”上。从此,我就成了先生的fans之一,先生有新的诗文问世,我都要一睹为快。 这期《收获》上先生的文章《金陵子弟江湖客》,是先生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母校南京大学(前身为金陵大学),回忆他在南京度过的童年、回忆他在金大求学经历的美文。 《金陵子弟江湖客》——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很有诗意,让人很容易想到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我也想起了我自己的一方印章:“休阳布衣吴中客”。 先生的行文字字珠玑,每处都能让读者感受到先生对故乡、对母校诚挚的爱。突然我读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江达灼”——这不是我们休宁中学八十年代的老校长吗? 余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较熟的同学,现在只记得李夜光、江达灼、程极明、高文美、吕霞、戎逸伦六位”、“江达灼是社会系”、“每逢课后兴起,一声吆集,李夜光、江达灼、高文美,几位双轮骑士就并驾齐驱,向玄武门驶去”云云。通篇提到“江达灼”先生的,全文有四处之多。这里的“江达灼”先生,当是余先生当年在金大就读时候一起办读书会讨论学问、一起驾着双轮在玄武湖畔驰骋的密友啊! 依稀记得以前翻阅休中校友录的介绍,江达灼老校长是解放前金陵大学社会系肄业。如此说来,我们休中的老校长,倒真的很可能就是余先生文中提到的大学密友了。不知道老校长是否知晓余先生在海峡那边,对他的殷殷思念? 贰 这次寒假归乡,我把余先生的这篇文章复印了几份,带回去给江老校长看。一下火车,稍作休整,我便去拜望老校长。老校长的家在县城一处安静的巷弄。我叩响老校长的家门,出来一位慈祥的长者。我很冒昧地介绍我自己,说我是年休中考取北大的那个同学,我的外公也是校长的学生云云。哪里知道老先生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不用介绍了,我很早就认识你了。” 原来江先生说我读高中时候,学校里有次讲座,当时已经退休的他作为嘉宾在主席台上坐着,见我在后排认真地听讲,还“弯下身子记着笔记”,就暗暗向当时的校长打听,记下了我的名字,说我是个“好苗子”。说来惭愧,其实那时,我对那个讲座不太感兴趣,在后排弓着身子读的却是架在膝盖上的《顾准文集》。惭愧,惭愧。不过,这个美丽的误会,也许就是我和老校长之间的缘分吧。 我问老校长:“您还记得余光中这个名字吗?” 老人沉默了片刻,说:“没有太大印象了。” 我跟老校长开玩笑:“人家余先生六十年后的文章里都惦记着您,您却把人家给忘记了。”我给老校长递上余先生那篇《金陵子弟江湖客》的文章,指着文中出现老校长名讳的地方,说:“这些都是余先生回忆您的。” 老人戴上老花镜,默默地读着他当年的伙伴六十年后回忆金大生活的文章。老人打开尘封了六十年的记忆闸门,跟我讲述当年的金大,当年的风风雨雨。 江老校长是在“国民政府”“还都”之后上的金陵大学,当年和余光中先生以及余先生文章中提到的数位先生都是要好的朋友。他们当时都是文学青年,兴致相投,就自发办起了一个读书会,隔周讨论读书的心得,阅读作品以汉译名著为主。吕叔湘先生的女儿吕霞也是他们读书会中的一员,他们往往将读书会的地点选在她的家里。江先生说,他们往往是隔周开读书会讨论,隔周去玄武湖畔郊游。老人激动的眼神里,我似乎读到了他与当年那干好朋友故地重游的憧憬。 可惜当日里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国之大,早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江先生是热血青年,参加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通缉,差点英勇就义,不过就此从金大除名,所以他最后一直是金陵大学肄业的文凭。江先生不得不作别金大,回到徽州,走上了休宁中学的讲台,和当年那干“双轮骑士”们从此天各一方。 我的外公是江先生在休宁中学任教时候届的老学生。我进门时候一时激动,都忘记向老校长转达外公对他的问候,这个时候才赶紧补上。老校长说:“你外公是我的学生,你爷爷还是我的难友呢。”当下,便问起我爷爷现在的情况。我轻声回答:“十多年前已经故去了。”老校长一阵沉默。 年“反右”的时候,学校里的工作组要求江先生揭发校长方怀毅的右派言论。江先生回答:“方怀毅同志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同志。”江先生端的是铮铮铁骨,为了那个大写的“人”字,坚决不出卖自己的良心,最终自己被打成“右派”身陷囹圄。在监狱里,他认识了我的“右派”爷爷。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江先生跟我说:“你爷爷当时身体不好,每天供应的口粮又少,干的活又多,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他比我还小三四岁,哪里知道怎么走得这么早―――”我恨我自己不坚强,我在老校长面前哽咽了,尽管我努力克制自己,但我还是哭出了声来。我请老人家原谅我的失态。 在老校长面前,我立下了宏愿:一定要尽快帮他和余光中先生联系上,让两位分别了快六十年的老人,在人生的晚景,好好叙叙旧。 叁 感谢台湾政治大学的彭立忠先生。他来北大作访问学者的时候,我们结下了深深的师生情谊。这次,他帮我打听到了余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余先生有江先生的消息,并电邮叮嘱我主动跟余先生联系。 我拨响了余先生的电话。 “您好,是余先生吗?” “我是。”话筒那头传来余先生平和的声音。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赶紧向先生问好,告诉他事情的原委,告诉他江先生的电话。 后来听江先生说,余先生马上打了过来,他们聊了几十分钟。但六十年的光阴,又哪里是几十分钟的电话能够诉得清楚的呢?只可惜我当时不在江先生的身旁,可惜我没有亲见江先生当时的激动和欣喜。 无线电波穿越“那湾浅浅的海峡”,江先生在这头,余先生在那头。 那可是穿越六十年时间隧道的声音啊。当年的青年,今天都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晚景。他们印象里的,只是对方年轻时候的面容。 那天晚上,我很兴奋。我把余先生的那篇《金陵子弟江湖客》又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读了一遍。 余先生端坐在金陵大学老图书室的红木靠背椅子上,他支着双肘,回想年轻时候的同伴:“我相信,若是我一个人来,只要在这被祟的空厅上坐得够久,李夜光、高文美、江达灼那一伙同学就会结束半个世纪捉迷藏的游戏,哇的一声,从隐身处一起跳出来迎我。” 现在,余先生的那一伙同学真的结束了半个世纪捉迷藏的游戏,一起出来迎他了。不知道余先生当晚有没有作诗,如果有的话,我想一定很美。 新安吴子桐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于北大 吴子桐赞赏 长按北京那家医院治白癜风最好白蒺藜图片
|
当前位置: 江达县 >海岛上的文字,终归要回到中原
时间:2018/7/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巅峰梦想围棋汽车拉力赛在桑珠洒咧
- 下一篇文章: 金钥匙假期旅行者最想挑战的地方,川藏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