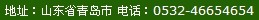|
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 ———纪念婺源“回皖运动”六十周年(-) █江湖一萍(江平) 本文本身未必学术,但本文归述的这份情结,或可引发徽学家、社会学者们作深入思考而学术;情结本身或许无价值,但若有关部门通过文字而间接体验,在以后的政区调整中能充分考虑文化因素,本文则具劝戒价值。 ——作者题记 公元年,唐朝置婺源县,属歙州;年,置祁门县、归德县;年,废归德县,歙州领黟、祁、婺、休、歙、绩六县——文史界常说的徽州“一府六县”,其格局实于此时既已奠立,此后就大抵稳定。 宋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婺源等六县共属一州府,长达一千多年。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渊源如此悠久,宗族、伦理、方言、习俗、学术、经济等等各方面的联系千丝万缕。作为大儒朱熹故里,婺源尤其被全徽州人引以为荣;作为皖派朴学奠基者江永故里,近代徽州学人对婺源又多一份亲敬。于是,婺源被改隶江西不仅是婺人的心病,也是全徽州人的遗憾;对于婺籍学人,则更是“一页痛史”——笔者作为新生代婺籍学人之一,于此也深深体验。在婺源“返徽运动”六十周年之际,谨以本文综述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纪念一份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域情怀,也表达类笔者之晚辈的文化乡愁。 █我们的祖辈——民国时期婺源人的“回皖运动”█ (江植棠先生-民国老照片。) 民国二十三年(年)蒋介石出于军事需要,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9月4日将婺源划隶江西省第五行政区。婺人极不愿脱离徽州!婺源百姓、民间团体与旅外婺侨及团体群起反对,纷纷上书请免改隶。改隶一周年的年9月12日在歙县发行的《徽声日报》上,发表了《婺各界为“九四”纪念告旅外同乡书》,力陈婺源划赣后政治状况“窳败不堪”。婺人视改隶江西的日子“九四”为“婺民一页痛史也”。年,婺源县参议会成立,上下串连,群情激奋,又发起“回皖运动”,一直闹到当时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呈文向蒋介石请愿。 由于“回皖运动”当事人早已作古,现在很难找到详尽的记载,但笔者年在《江淮文史》上发表长文《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后,歙县长辈方少求先生特意寄来了毕业于民国中央大学、曾任歙县中学校长的耄耋老人程极平先生知晓的信息,并表达了自身对老徽州的情感,去年笔者又亲赴徽州故地走访过江达灼、孙思诚等老人,遂得知某些细节。“回皖运动”是在徽州民众、尤其各地婺人普遍要求婺源返徽之情势下展开的,声势浩大。崇尚“理学渊源”、“读朱子之节,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的徽州人向来注重文化根基,彼此认同感很强,何况徽州人对朱子故里婺源历来多一层看重,岂可割舍婺源?又何况在六县各有的“属相”中婺源恰恰属龙,怎堪龙脉分离?当时的省立徽州师范首任校长江植棠(90高龄的徽师校友柯敦厚对江植棠推崇备至)、第三任校长查景韩(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等婺源籍名士,是该运动核心领头人,各地婺源同乡会积极配合。作为屯溪茶市主力的婺源茶商更是 满怀期望地参与,有的茶商公然在敬客的茶碗上刻印“回皖”,想必是用谐音,耐人寻味。孙思诚父亲孙友樵(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开着“怡新祥”茶号,就是参与者之一。即便政府已经将婺源划入江西,但各地婺籍商人并不认可,他们的名片、信封还坚持印上“徽州”或“安徽”字样。而整个徽州商帮也不承认婺源人是江西人,王振忠先生《徽商的一张身份证》(年11月1日《中华读书报》)记有上海“徽宁会馆”年为婺源墨商开具的证明书依然认可“同乡詹天骅”,即是一证。“回皖运动”时期,婺源县内一般乡绅与民众也纷纷响应,连笔者家父吃过的江湾月饼上也出现过类似“返徽”的字样,谐“返辉”也欤?一些学校大门口还贴出对联:“男要回皖,女要回皖,男男女女都要回皖;生不隶赣,死不隶赣,生生死死决不隶赣。”甚至更有急切口号:“头可断,血可流,不回安徽誓不休!”……六十年过去了,追溯这样往事,心情焉得平静?隶属调整乃常见行政举措,而一个县的民众如此强烈要求归属原区的先例,别地实不多见。据说“返皖运动”的宣言甚至拟照《国父遗嘱》云:“我安徽省徽州婺源县,向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程朱之阙里,中华之奥区。今日沦入赣人之手,实我皖人之第一大省耻。为今之计,必当唤起民众,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外省人,驱逐老表,恢复河山。”这样的言辞固然伤及赣人,但可想而知婺源人对徽州感情的深挚程度。据程极平老人说,最终经江植棠等与婺源“明经胡”后裔、绩溪人胡适先生向蒋介石一再请求,促使国民党内政部派来婺勘察。台湾出版的胡适秘书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页,记有胡适在民国五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一段话: (胡适)先生又说:“徽州的婺源,朱夫子的出生地。……划给江西省;可是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一直闹到复员之后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作好呈文要向蒋介石请愿。我说:?给我吧。?我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张厉生。那时张厉生是内政部长,他就照办了。”先生笑着说:“这是帝国主义的做法,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按:原文如此)划归江西,他们还把二程先生的祖先还算是徽州人呢!……” 经蒋介石同意,年8月16日,婺源总算划回安徽省。《休宁县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当时海阳、屯溪等地徽州人闻讯后的欢欣庆贺,更不必说婺源人自己心里那个高兴了。年5月,解放了的婺源再次隶属江西省至今。黄景钧先生云:“解放婺源的是解放军的四野,和解放江西的同属一支部队,为了军事管理的方便,当时又把婺源划归江西。”查《徽州地区简志》与《婺源县志》,当时解放婺源的其实是“二野”部队,而屯溪那边,也是“二野”三兵团进驻。8月“二野”留驻婺源的工作人员要开赴大西南,才由“四野”部队派员来接管。这里面,转给“四野”接管的具体原因是个谜。程极平老人有陈述:“到新中国成立时,徽州专署已决定派杨建图(后任徽州专署教育科长)及歙县的吕卿等人前去婺源接收。不料江西方面领导人已经接收了。婺源县的归属问题从此成了一个历史问题。” █我们的父辈——新中国第一批婺源学人的“返徽”心愿█ (黄景钧先生年生于婺源,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婺源的归属问题,江植棠、查景韩等笔者祖辈学人为之奔波得愿而终究落空;解放后,作为曾经在旧政府学堂任职、与胡适之类旧文人有染、又多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的他们,面临风云变革,显然不再能出头。哪怕受政府重任的,如婺源人、现代中医名家程门雪,身为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即便也深怀徽州情结一直自称“皖南程氏”,但在那样的气候下也不敢如昔日的江植棠那般直言。 待到我们父辈时,都已在政治挂帅氛围下生存。贫苦出身的一般民众政治上获得了地位,对政府绝对顺从,原本于徽州文化了解就少、加上盲目反封建的思想灌输,更关键是原来与徽州的经济联系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完全没有了必要,于是造成他们急着返归徽州的心情相对松缓了。 制度更替,然而,千百年相沿的崇文尚礼的民风依旧。婺源周边几个县市与婺源接邻处长期存在冲突乃至发生械斗,先动粗的也往往不是婺源人——依此而论,前文中婺源民众上书蒋介石所担心的“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大都民风强悍,勇于私斗,寻仇报复,法令几不能制止,若划婺入赣,将不胜恶化”并非空穴来风,隐在矛盾至解放后依然是存在。我们父辈的一般民众至少从民风上还是对江西不尽认同、而于徽州每每怀念的。即便在隶赣已经半个世纪的年,凤凰卫视在婺源摄制《寻找远去的家园》电视专题片中的记者到婺源采访时,老辈的村民还说:“他们是老俵,他们冬天在房间里烧这么大的柴火取暖;我们用小火炉,手炉。……过去挑担,这里到屯溪每四里路就一个茶亭,徽州都一样的。他们江西就没有,江西卖都不卖给你吃。”或许语气中对江西似有成见,但这些不加修饰的话语透出的情感十分真实,正可见连不识字的婺源老农民至今仍视江西为“他乡”而对徽州风俗尤其自豪,遑论文化人了。 义务教育使得我们众多的父辈能上学,但不再是读私塾的经书,而只是识字、诵读革命语录,或者学工农基础知识;只有那些幼年在书香门第中略读过诗书、爱好文史的少数父辈,以及聪慧与机遇兼得、文革前大学毕业或文革刚结束以大龄考入大学终于了解到昔日徽州才俊之星灿、文化之辉煌以及我县与徽州历史文化渊源的少数父辈,才会情不自禁时常在内心深处喟然长叹:“婺源的归属问题成了一个历史问题!”——这正如曩昔负笈于民国中央大学的程极平老人的叹息,这更是查景韩的儿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查秉枢先生的叹息。也许是因为父亲查景韩是民国年间婺源“回皖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尽管查秉枢先生已经退休,但他一直怀着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婺源返徽”的心愿、至今仍在致力于此。 有别于旧时的“回皖运动”,“婺源返徽”又多出一层心志。年11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安徽省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批复》,撤消徽州地区、设立地级黄山市,将绩溪划归宣州地区。如果说失去婺源的徽州只是残缺的徽州,则自此日已经不复徽州!——“婺源返徽”的二层心志:其一,恢复地级政区“徽州”;其二,婺源与绩溪同返徽州、恢复“一府六县”。 绩溪是婺源的“难弟”。绩溪的父辈学人类似的返徽心愿同样感人。年夏,笔者游访绩溪,与章亚光老先生面晤。章老怀有强烈而深挚的返徽心愿,从绩溪划入宣州之日起,这位坚韧的长辈就一直坚持不懈地为返徽心愿奔走疾呼!他将自己近20年里大量的文稿与信访材料编辑成册印行,笔者读之,感其哀鸣,每掩卷浩叹。章老退休前是法官,他的《徽州更名黄山和绩溪划出徽州的法律透视》一文(《合肥学院学报》年社科版第1期)批驳支解、消亡“徽州”之种种不合法与诸多弊端,有理有据、论述得相当充分。 要求“恢复徽州”的论文、呼吁、提案在安徽省内已经很多,正式向中央一级提交的提案则似未见;年——在婺源“返徽运动”60周年之际,终于有了新进展。1月9日、10日《北京晚报》连载黄景钧先生的文章《婺源归属》,该文结尾:“我建议将黄山市改为徽州市,置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归徽州市管辖,这对于发掘、发扬徽文化,振兴皖赣经济乃至振兴我国中部经济都是很有帮助的。”徽州故地学人奔走相告,《新安晚报》迅速就有响应文章。 黄景钧先生年生于婺源,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央民盟法制委员会主任,至今连续三届为全国政协委员。年在政协提交提案掀起了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同年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收容遣送办法》。年3月,黄景钧、弥松颐正式向全国政协联名提交提案《关于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成立徽州地级市的建议》。 这个提案重点分析了恢复徽州后的经济或社会意义。在政府眼里,权衡问题的主次顺序一般是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学人提案,“政治”当然也可以提几句,但用不着学人多说;如果主要提“文化”情结,刺激政府上层官员作为人之常情的那根心弦,用处也不是丝毫没有,只是政要们往往不会很当一回事;所以,强调“经济”意义,不失为提案的一个好支点。我还认为这个提案的重要作用,在于以正式的形式使中央听到民间(当然主要代表着学人)的呼吁。不要说黄老等老一辈学人,就是我们这样的小书生也心里也明白,中央单独为恢复徽州而特意调整相关区划的可能性极小,除非乘着全国性的区划改革之大风。但如果中央听不到足够的民间呼吁,即使有大风来了,上层也未必会考虑徽州故地这一块的特殊背景而做什么调整。随着民间合理性呼吁的上达,一旦全国性区划调整启动,婺源与徽州别县的团聚就极为可能。基于这一观点,一萍认为该正式提案不管能否在近期落实,均有重要作用。当然,该提案骨子里深浸着的,显然还是文化情结,这才是实际的提案动因。黄老等是长期生活在京城的老一辈学人,有生之年相对有限,他们的某些心情也更急切一些;弥松颐先生不是徽州人,但他理解徽州人的情结并参与呼吁,很值得敬重。 █徽州,我们的故乡!——新生代婺源后学割不断的徽文化乡愁█ (本文作者江湖一萍) 昔日婺源各团体请免改隶之理由中,习俗、文化、历史三方面的依然存在。婺源至南京、上海、杭州的客车一直就是穿过徽州故地的;高校扩招与民工潮,使得近10年来大量婺源青年沿途目睹到唯有徽州故地的几个县才与我县风物相似,甚至误认某村是故乡。随着婺徽、徽杭高速公路的通车,我县经济上与屯溪一带的联系也将更趋紧密。年秋,笔者以婺源后学身份在《江淮文史》季刊发表长文《徽州,我们的故乡!--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或许是建国后婺源人第一次系统地梳理我县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并公开地表达徽州情结。作为作者,我只是想陈述事实、表达一份真切而特殊的文化情感;这样的“情结”值得学术界研究,对于行政规划来说,也不无劝戒意义。 后来,笔者才知此文被很多徽州前辈读到,并有若干老先生特意来信“深表同感”并热情鼓励,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这本身也至少表明两点:首先,“徽州情结”为六县学人所共有;其次,徽州前辈学人也许曾担忧“代沟”会割断心志的传承、担心时间将使后辈逐渐认可现状,而笔者这类徽州后学的徽文化情结使他们感到了安慰。细细想来,或许还另有隐在的第三点:徽州别县的前辈学人对于被强行割离的朱子故里、徽州师范创始人江植棠故里婺源,原本就多一份追怀、多一份悲情,何况入赣已经半个多世纪、料想新生代婺源后学并不会对老徽州有感情,而笔者的“渊源与情结”文字令他们尤感意外,于是更多一份别样的欣悦。 徽学、“徽文化热”方兴未艾,直接引发一般婺源青年对“一府六县”认同的,是不断推出的介绍徽州的电视片;文化界的婺籍后学则主要凭着书籍图册与互联网深化了对徽州文化、对家乡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之认识。身在家乡的婺源后学,多在文教系统,均不同程度怀有徽州情结。中学的青年历史教师更利用专业、职业以及互联网优势,积极普及与讨论徽文化。清华中学教历史的吴老师,骑摩托车踏遍徽州,拍摄大批照片,还写下一路的随想。到绩溪时他写着:“特意选择来上庄是因了胡适的缘故。……当年婺源回皖,我们需要感谢胡适。徽州的概念正慢慢地从一般民众脑子里淡薄下去,恢复徽州地理也遥遥无期,一般的年轻人对徽州的认同也在逐渐淡漠。今天还有胡适这样的人吗?”身在外地的青年学人,怀乡尤切,更亲身感受到徽州这块区域较之别地之诸多可贵。笔者周围的学生、同学、同事们无不是从我口中,才逐步了解徽州。甚至他们也有“染上”徽州情结的,总嚷着要我带路到徽州故地探访。短短数年内,婺源旅外后学自办的网站多达一、二十家,抒发乡情不足为奇,但无不北京哪家医院看白癜风最好海口治疗白癜风医院
|
当前位置: 江达县 >江平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
时间:2018/1/1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雪巴沟,横断山深处的小亚丁
- 下一篇文章: 新闻动态西藏昌都发现距今约2000年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