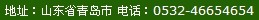|
今天不给大家介绍景点,而是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一本回忆录,名叫《艽野尘梦》。这本书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湘西王”陈渠珍年赋闲长沙时回忆其年至年进出西藏生死经历的文言笔记体纪实作品。书中所描述的藏区险峻优美的自然风景,古老淳朴的民俗风情,复杂险恶的官场环境,身陷绝境的人性异化,绝地逃生的生存智慧,藏汉人民的深厚情谊,感人至深的爱情绝唱,堪称奇绝。这本书被誉为民国奇书,是解放军18路军进藏参考读物之一。 寻找这样一段西藏往事,仿若再度经历一场艰苦的藏地穿越,亦真亦幻;路过一位阳光般灿烂的藏族女孩,亦悲亦欢;最后一头撞进一个烽烟弥漫的动荡时代,亦幸亦哀。 一个男人的西藏往事,在他走出羌塘24年后,在一个秋天缓缓展开。那里有着雪山草地的雄奇辽远,有着惊险疲倦的异域征伐,有着九死一生的漫长归途。当然,这一切,冥冥中,仿佛都只是为了与一个藏族少女的遇见。 那么,就让时光重回第一次相遇的那一刻:草尖上都泛着光珠儿,西藏江南——林芝。一群藏族少年英姿飒爽,身手敏健,正在表演传统的“骑马拔竿”游戏。其中一人连拔五竿,引得一片喝彩。在那喧闹的人群中,年轻的汉族军官多看了那少年一眼,却见他羞涩莞尔,皓齿明眸。一旁的藏官乘机进言:她本女儿身,是自己的侄女,如果喜欢,不妨就让她随军伺候大人。 只道是戏言,不料却是听者无意,说者有心。几天后,风华正茂的汉族军官迎娶了含苞待放的藏族贵裔女。 那一年,男人27,女孩16。 那一年,年,川军入藏平叛,辛亥革命还未发生,时代的变革却迫在眉睫。 男人在短暂的驻防后,再度开拔。在一场又一场剿灭藏地叛乱部落的时日里,藏女已经不再是一个女孩,而是随夫出征的女人;她也不仅是一个女人,而是帮助夫君逢凶化吉的战士。她在男人月下巡岗时挎刀随行;在敌人向男人射出子弹之前率先惊呼示警;在男人腹背受敌之际率先跳崖突围,只为回接紧随而下的男人;在辛亥事变之后,入藏清军哗变,帮派深度搅局,男人进退失据,性命堪忧,只能选择返回远在湘西的“故乡之城”。 她没有犹豫,因为他是她俗世中的“神”与“信仰”。阿妈含泪送别,留下一座八寸“珊瑚山”作为纪念:“无论在哪里,只要想阿妈了,就多看看珊瑚山吧,看到它就如同看到阿妈和故乡!”雪山、圣湖、经幡、还有喇嘛庙,一切都远了,男人集结了名亲信兵卒,开始了一段中国式的“出埃及记”。 他们误入羌塘大漠,迷路、缺粮、风雪、野狼等,恶劣的环境和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终于为人性的丑陋准备好了充分的舞台:队伍里有人掉队再也找不回来,有人为被狼吃剩下的同伴骨肉而大打出手,有人想杀了皮包骨头的藏族男孩,有人偷袭途中施舍自己粮食的喇嘛却反而丢了性命。 但是,这所有的残酷和惨烈却因为藏女的存在,而没有发生在男人身上。女人生长于藏地,更懂得荒野迷路后的生存法则,她为男人打猎,也频频将险失人性底线的士卒重新拉回正常的轨道;她教他们如何在风雪中储制干粮,也将活着走出羌塘的希望传递给越来越绝望的男人。她把最后一块肉干给男人,仅仅因为“这个世上可以没有她,却不可以没有他”;她在狼群出现的危险时刻,紧紧抱住男人,也试图保护住男人。在茫茫大漠,女人最终成了男人的“神”,也成了他要坚持活着走出羌塘的“信仰”。 最终,整整7个月,幸存7人,完成了这漫长的生死穿越。男人与女人辗转流落到西安,在此等候湘西老家汇钱回湘。彼时,行李空空,穷困潦倒。 阿妈留下的珊瑚山当了,使用多年的军事望远镜当了,每每男人外出寻人找事,女人总是在侧门呆坐一天,守候男人的归来。 直到有一天,男人回家,发现女人面容绯红,浑身发热,情急之下,求请医生,却误诊为伤寒,用药之后,即起天花,不日发黑,全身浮肿,死局已定。 男人嚎啕大哭。那么多命悬一线的时刻都已度过,那么多漫长的艰难归途都已走过,那么多相守一生的承诺都已许过,为何却要在这一刻永远“告别”!在这凄凉的异乡,一个藏族女孩在乱世中死去,她短暂的一生难道就是为了那场美丽的遇见,以及对于这个汉族男人生死一线间的守护? 她满噙泪水,给男人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的告白:“万里从君,相期终始,不图病入膏肓,中道永诀。然君幸获济,我死亦瞑目矣。今家书旦晚可至,愿君归途珍重。” 那一年,男人29,女人18。 那一年,年,民国初建,中原烽烟阵阵,渴望建功立业者往往只能归于漂泊和逃亡。 男人终于回到故乡。在“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的大时代,他终于崛起于那片霸蛮之地,并称雄数十余载,史称“湘西王”。年,他将藏女遗骸迎回故乡,亲撰墓志铭。年秋,受湘省军阀政治暗算,在长沙赋闲之际,追书24年前的藏地旧梦,他在终笔之处仍涕泪泣血:“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 再过15年,,男人因病去世;7年之后,藏女墓地被平,至此魂归无处。在这样的“白露”秋夜,重新翻读这样一段西藏往事,仍像第一次看一样,仿若再度经历一场艰苦的藏地穿越,亦真亦幻;路过一位阳光般灿烂的藏族女孩,亦悲亦欢;最后一头撞进一个烽烟弥漫的动荡时代,亦幸亦哀。 那个男人叫陈渠珍 曾为贺龙的长官和对手 而他的文武韬略则深深影响了其手下的文书——沈从文 那个藏族女孩叫西原 除了存在于陈渠珍的回忆录里 她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遗物和相片 那本回忆录叫《艽野尘梦》 被誉为民国奇书 解放军18路军进藏参考读物之一 如何评价《艽野尘梦》这本书?回答者:知乎网友豆子起初看《艽野尘梦》,是奔着传说中的爱情去的,想看看那个誓死保护他的藏女,那个成功东归却暴死的西原。 除此之外,便是怀乡。 作者随军入藏,起初在江达,看见了藏番出兵,往来蹂躏后,极目荒凉的街市。也碰见了一个名叫保林的成都人,他入藏已经二十余年,见陈渠珍来,很是殷勤。他想要在军中谋个差事,不为薪,不为酬,自然也没想要飞黄腾达。他只是想念自己的母亲,那个远在成都,日日思念他的八十岁的女人。他的妻子也五十多岁了,为陈渠珍他们准备了家里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这些卑微如草芥,飘摇如浮尘的人啊,倘使不载入这本回忆录里,又有谁去在意他们的愿望呢? 还有去往青海的路上,碰见了一个精神矍铄的老番人,领着五六个小孩。他说他是湖南湘阴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年轻的时候跟着左宗棠出关,流落不能归乡,只好在青海安家。他娶了藏女,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孩子。老头儿没什么可以相赠的,让小孙子跑去拿十几个鸡蛋送给陈渠珍。第二天,当陈渠珍告辞的时候,问老人家:“老人何日归?”老人长叹:“乡音久改,鬓毛已衰,来时故旧,凋零不通音讯,已六十年矣。今纵化鹤归去,恐亦人物全非。儿孙在此,相依为命,君问归期,我归无期矣。”六十年风光倏忽而过,三千里亲朋全赴凋零,纵然是回去了,那些故人也大半已化作了鬼魂。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啊,我回不去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作者决计领着湖南同乡和自己的亲信东归。一番艰险,误入荒漠,断粮七月,几丧人性。众人沿途死亡抑或失踪,能跟着作者一起活着回到西安的,仅七人而已。 斯人已逝,万物归寂。 留给后人的,没有碧血,唯有青山。 李某某这本书真是精彩而又冷酷,充满了动荡时代的各种无奈。尤其是处于一个民族矛盾激烈的时候。 不仅川兵平叛杀了许多藏人,还不乏军纪败坏的事,藏族头目投降了,还要诱杀,东归时的喇嘛向导不堪士兵拳打脚踢,宁愿离队而葬身狼腹。 藏兵也不断报复汉人,各兵站都被藏人屠杀,连和汉人有过密交往的也一并对待,西原父母就是这样惨死。而辛亥爆发,川军又杀死军队的旗人,蒙古喇嘛救了他们,却又因贪念劫掠蒙古喇嘛。西宁到兰州时,又见西北回民,马家军欺压无辜的汉人。 可以说,这本小说,看到的是一个人命不值钱的时代,一个民族相互报复的时代。人在乱世里头,命是贱如蝼蚁。 More每个时代都脱不了爱情,如《艽野尘梦》的主人公陈渠珍和西原。令人肝颤心疼的藏女西原,好一个心念你若娶我,我便生死相依。 薄薄的一本书,《艽野尘梦》一开始就怀着敬畏之心。对于被现代快餐文化侵蚀的人来说,文言文读起来费心费事费力,文字满天飞的时代,一篇看似好文的东西随手就来,稍不顺心,顷刻抛弃于九霄云外。一开始,只是读。理清事出何人,事因何由,事发何地,难免枯燥,还得不是百度百科一些生僻怪字,着实无味。行兵打仗确实激愤人心,但在我心里,偶尔的风景描述,人文风俗更为有趣。 川军入藏,免不了打打杀杀,兵家胜败,你进我退,你退我追。行文至半,即将开始逃亡之旅。战争早已被时代的洪流淹没,如今读下来,更多人白殿风方法中科白殿疯医院
|
当前位置: 江达县 >它是民国奇书,它是18路军进藏参考读物,
时间:2017/12/3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